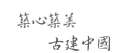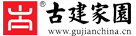本科畢業(yè)之前一直是一個非常懵懂的狀態(tài)。那時候的學(xué)習(xí)沒有大量的知識面,在有限的知識里會有些彷徨,整個大學(xué)都沒有正兒八經(jīng)地研究一個小建筑,對單體的建筑興趣不大。大五畢業(yè)設(shè)計做了一個上海內(nèi)城老城廂設(shè)計改造,開始傾向于城市設(shè)計。
“這可能和那時候的環(huán)境有關(guān)系,97年上大學(xué),一開始接觸的都是安藤與現(xiàn)代主義這樣的一些信息,實際上那時候看都看不懂,也沒幾個老師懂科普,沒幾個老師懂造房子,幾乎就是自學(xué)的一種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下,我對建筑的兩方面比較感興趣,一是它的文化性,另外一個是它的社會性。
小時候傳統(tǒng)文化比較感興趣,愛好寫字、畫畫,大二做的第一個純中式室內(nèi)裝修設(shè)計就帶了許多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同濟老師宣傳邁耶的那種風(fēng)格,局部素材偏向現(xiàn)代主義,整體藝術(shù)震撼人心,對文化性的理解也朝著現(xiàn)代主義開始轉(zhuǎn)變。大學(xué)的后面幾年也對社會住宅或者一些大型公建感興趣,它們或多或少帶有社會性。
之后借了一筆錢去德國留學(xué)。可是到德國第一天,就有點后悔了,一點也不喜歡那的風(fēng)土人情,房屋設(shè)計也是一種產(chǎn)品主義的氣質(zhì),構(gòu)造太緊,沒有松度和詩意。還有,這地方的姑娘也不是我喜歡的樣子。在德國跟著一位比較有名的搞城市設(shè)計的教授,那時候發(fā)表了很多大型的城市研究。
在那里學(xué)習(xí),一方面可以思考中國整個城市建設(shè)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也能多關(guān)注大體量、多體量建筑的改造和新建,都可以和社會發(fā)生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德國三年半里的一個暑假,去了荷蘭鹿特丹一個月,因為那邊有一個大學(xué)同學(xué)上學(xué),這一個月很短,卻是留學(xué)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階段。我接觸了荷蘭的一些思想,相對于荷蘭來說,德國比較保守,還是以傳統(tǒng)建筑學(xué)的方式來操作一個城鎮(zhèn)如何生成。到了荷蘭看到那的老師用類似大數(shù)據(jù)制造的方式去教學(xué)生去操作一個半邊城市的生成。
“這種半邊城市的生成對我的沖擊很大,我覺得它比人為做決定會更加理性。因為城市的數(shù)據(jù)、容量正變得越來越復(fù)雜,它是產(chǎn)生合理性的一種替換。但同時也對它抱有一種批判態(tài)度,我一直認(rèn)為城市的建造或者城市的生存永遠是跟城市的數(shù)據(jù)、社會狀態(tài)、文化偏好有關(guān)系,但實際上沒有那么簡單,單一的因素?zé)o法起決定作用。所以在去了荷蘭之后,更傾向于如何去分析當(dāng)代都市的一些復(fù)雜因素。
數(shù)據(jù)只是其中一個,也包括商業(yè)、人流、基礎(chǔ)設(shè)施等等。那時候在德國做了很多城市設(shè)計,其中很重要的幾個概念就是基礎(chǔ)設(shè)施、景觀設(shè)施和交通系統(tǒng)等等,始終把它們放在第一位,而把建筑一直放在第二位。這樣的思想不涉及到建筑本體如何去營造,根本不關(guān)心建筑的材料和結(jié)構(gòu)。
在德國的畢業(yè)設(shè)計做的是一個類似都市的宗教中心,是一個超高層的設(shè)置。它反映了我當(dāng)時堅持的想法,我認(rèn)為都市文化里的宗教文化很重要,會影響一個都市或者一個城鎮(zhèn)的生成。大學(xué)時期就是在這種激進與保守之間,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做思想斗爭,抵達一個廣闊的視野。到碩士快結(jié)束的時候,還是從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層面來考慮建筑的問題。”
回國以后,從2005年底到2010年一直在設(shè)計院里,那時候有一個觀點,認(rèn)為要從城市層面看待建筑,意味著要去從城市層面操作建筑,這種建筑體量就非常大。而當(dāng)時只有大型的知名設(shè)計院才有可能接觸到大體量。那時候留學(xué)生普遍的選擇是要么在國外工作幾年,要么就在國內(nèi)找非常好的外資單位做設(shè)計。
如果選擇國外事務(wù)所,做的永遠是流水線上非常小的一塊,一個留學(xué)生對國外事務(wù)所來講沒有什么太大的期待,而選擇國營設(shè)計院,對方案能力和開發(fā)度都是一種很不錯的鍛煉。2005年前,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年輕設(shè)計師進入國營設(shè)計院,很有可能接到非常大的任務(wù),由于人手不夠,每個人可能分到一個難以想象的大項目,比如城市最佳實踐區(qū),或者江南船廠改造等等,都是上幾萬方的體量,這樣的機會對一個年輕設(shè)計師來講,可以說是稍縱即逝。
“設(shè)計院中標(biāo)之后,我也抓住了機會,負(fù)責(zé)建筑方面的施工圖,不懂的就請教那些老前輩,請教材料商,請教各種各樣的結(jié)構(gòu)工程師。在半自助的情況下,算是把項目完成了。在這個過程中也看到了好多國際大型事務(wù)所做世博會的過程,他們的圖紙的水平,對建筑的理解,爭奇斗艷的非常炫技化的一些手法,這些東西就像走馬觀花一樣給了我強烈的刺激。即所謂的大項目,它不代表可以灌注很多文化性和社會性。很多時候越大的項目就被關(guān)注的越多,拍板的領(lǐng)導(dǎo)層次越高,項目就越要迎合資本去做。
另外一方面啟示我年輕建筑師不能做大項目,做大項目會把很多短板暴露出來,對系統(tǒng)的思考,室內(nèi)室外設(shè)計的成熟程度等等,如果非要給年輕建筑師做,需要一個很長的周期,可以先去思考,去參觀,再考慮去改良。這也是我們國內(nèi)非常大的一個誤區(qū),一幫在設(shè)計院的設(shè)計天才往往會陷入一種對好項目的渴望當(dāng)中,然而他們沒有能力去完成一個獨具風(fēng)格的作品,沒有能力給予一個項目生命感。年輕建筑師還容易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比如說來自于總建筑師,來自于領(lǐng)導(dǎo),來自于各個甲方,如果一個很小的孩子可能無法協(xié)調(diào)壓力去解決這些問題。
雖然我的很多渴望沒能在設(shè)計院得到足夠的釋放,但也算對中國整體的項目狀態(tài)有了判斷,了解城市大體量、小體量項目意味著什么,有些項目大量借助于外部政治與資本的勾兌,那不是建筑師能夠控制的。這意味著一些看似非常好的時候,它只是有一種美好的外在,本質(zhì)上可能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它在表達的層面上已經(jīng)被局限了,頂多可以拍幾張照片上上雜志。高標(biāo)準(zhǔn)一點來講,它在立場上對建筑本體的思考就是不夠的。院里的這五年就像煉獄一樣,在不停地在鍛煉、錘煉我的價值觀。
“在設(shè)計院的時候也做很多城市研究。比如說北京、上海的城市研究,算是在設(shè)計院的一個副業(yè)。做城市研究就會對許多現(xiàn)象保持一種批判性,很多建筑師長時間做項目就會飄飄然,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很牛。但實際上是很浮夸的,在周邊的同行里可能還算可以,但是如果把他的東西放在中國的一個社會環(huán)境里面,它有可能還不如一個設(shè)計院做的一個大型項目有價值。
一方面它沒有社會意義,另一方面從本體角度來講,在世界的范圍里它的格局又不夠大,外國人看到這種東西會覺得怎么和他們那么相似,在世界范圍內(nèi)同樣沒有文化意義,或者說它不具備原創(chuàng)性。那么就形成了浮夸,所謂的浮夸不是說這些東西本身做得不夠好,而在于從社會視角上看,它有沒有一種與社會相關(guān)的親密感,是否忠實的反映了中國的現(xiàn)狀而并非去矯飾社會的現(xiàn)象。
在世界建筑師的格局里面,是否做了一種非常獨特的原創(chuàng),而不是說延續(xù)某一個大師某一個流派的東西。這兩個標(biāo)準(zhǔn)也在永遠警醒著我,做某些項目的時候,它到底有多少價值。
如果沒有這兩個標(biāo)準(zhǔn),表面上的成功是很短暫的。過了五十年有可能大家會看你的作品,會認(rèn)為還不錯,這才算做持續(xù)的成功。可能這種定位比較苛刻,但是前提就在于無論如何要保持一種敬畏之心,很多時候我們做的東西很有可能就是前輩做過的,也有可能是一些玩剩的把式。只是你在項目中不停的努力才覺得自己很開心,本質(zhì)上看這種項目多一個少一個都無所謂。
至少要有一個有個執(zhí)念,或者要有一個立場,建筑就是這個立場,它不服務(wù)于你的現(xiàn)狀,它應(yīng)該服務(wù)于一種永恒性的東西,可能是一種生活方式,可能是一種傳統(tǒng),也可能是一種習(xí)俗。建筑師的作品看多了,很容易看出他們堅持什么東西。比如劉家琨老師會比較喜歡做一種地域特色的營造,但是這不代表他不懂那些炫技的手法,他堅持的是一種立場。
那么要堅持,就首先學(xué)會克制,不去選擇炫技那些沒有意義的方法,盡量通過簡單的辦法解決問題。還有就是做出建筑的生命,因為建筑就是露體、色相的東西,能看到顏色、形式以及各種各樣的材料。但是它背后是有靈魂的,這個靈魂會表達出某一種狀態(tài),每個人都能看到,它可能是清高、可能是對社會有一種批判、也可能是保持某種繁榮。
在考慮建筑靈魂的時候,我們心中也有一個“穴”。會考慮房子在都市里面、村落里面它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它要表達怎樣的立場,或者房子與房子之間形成哪些重要的串聯(lián)。可以這么想,如果把自己的一些作品梳理起來,它可能形成一個完整的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如果把這十個東西放在一起組成一個村,你不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參差不齊的奇花異草,反而相互之間都有關(guān)系。
這就形成了一個系列,這個系列它還在不停的變化,但是如果把所有東西收集在一起,能看得出它整體的和諧。比如說十年前的A房子、五年前的B房子和現(xiàn)在做的C房子,三套房子放在一起,會發(fā)現(xiàn)空間方面有一些想法的變化,但是骨子里面一定有一個在現(xiàn)實中一直堅持的東西。這就是所謂的靈魂,不是一個房子決定的,是一系列房子整體的呈現(xiàn)。”
在設(shè)計院做到了一零年底,一一年初就辭職了。早年有些積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向做建筑了。對建筑系統(tǒng)性的一些基本知識的積累到那么多的對城市方面的研究,給我了社會的真實面,這也就決定了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選擇做什么樣的東西。
創(chuàng)業(yè)伊始我們主要是做所謂的“熟人圈”的東西,這也是因為早前研究得出的結(jié)論,中國的熟人圈很重要。所謂“熟人圈”比如潮汕人做生意就很典型,向熟人借錢的時候不需要擔(dān)保人,因為彼此信任有人愿意把錢交給你,按時還錢就可以。如果關(guān)系不熟這個事情就很難做。
中國疆域太大,雖然我們講中國是一個國家,可相對于歐洲來看,中國有三十幾個“國家”,地域之間的習(xí)慣和信任感是不同的,開放狀態(tài)和財富狀態(tài)也不一樣,對一件事情的理解也不太一樣。但并不代表越有錢越開放,像我老家浙江這樣的地方,有好多朋友親戚都住在浙江最開放的城市寧波,他們早些年的住宅還是很不錯的。
我們一零年做了一些住宅都是非常現(xiàn)代的。現(xiàn)在回頭看,就覺得好像一把鋒利的刀一樣,雖然它有些地方不完整,或者有些地方有缺陷。但它沒有拖泥帶水的狀態(tài),很決絕,不會打算做的更溫柔一點。只要你有適當(dāng)?shù)氖覂?nèi)裝修技巧,一般裝修公司都可以做到溫柔一點,舒服一點,溫馨一點,豪華一點,但我們那時就是很堅決,很簡約。這里面實際帶有強烈的批判性,或者說代表了一種立場:我們要的就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雖然這種生活方式當(dāng)初有可能未必適合我們那些甲方,但是至少他們接受,他們也生活在里面,并沒有完全抵觸這樣的方式。這件事情很有意味,我們做住宅,是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不再追求那種大的項目,不再追求那種看上去非常復(fù)雜的甲方關(guān)系。要追求一種單純的甲方關(guān)系,去追求一種熟人圈的甲方關(guān)系,他們能放心地把房子交給我,才能做我最想做的東西。
現(xiàn)在許多的年輕建筑師正在做一些很甜蜜的房子。然而這個年紀(jì)需要的是一種非常明確的目標(biāo),或者說非常果敢、勇敢的狀態(tài)。如果做的很甜蜜,會給現(xiàn)在的年輕建筑師帶來傷害的,現(xiàn)在好多民宿像是個機會,但民宿一做多,建筑師就容易在最有力量的時候,變得很溫柔、很油膩,漸漸變得沒有價值。
早年,我們做的是青紅磚的或者木構(gòu)的,還做混凝土那樣非常明確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西。要傳播現(xiàn)代主義的建筑,住宅可能是一種最好的方式。因為住宅跟人的日常行為發(fā)生關(guān)系。比如看一個公建,不可能躺著去看這個公建,不會在公建里洗澡,更無法感受到公建一年四季的變化。
要看一個博物館,最多一年去十次,看到的永遠是它最好看的那一面,但我們不知道這個房子可能有很多缺點,不會把這個博物館當(dāng)成自己的一件事情。而住宅它會變成我們的盤背,就像駕車一樣,會關(guān)心它哪里壞了,會在方方面面去體驗,找到它的適應(yīng)性狀態(tài)。
如果住戶有反饋給我,也會很開心,因為他們在乎這個房子。而不是說我們進入一個圖書館,一點感情也沒有,這房子跟我沒關(guān)系,館長長得再有型跟我也沒關(guān)系,也許會罵這破房子怎么借個書這么困難。那樣的建筑沒有情感性,不會給人們帶來教育。而在一個村里做住宅的話,整個村里面的人都會對它評頭論足,有一部分人在罵,一部分人覺得還可以,這都挺好的。因為它被放在一個村里面,就影響了村里面的思維方式。村民未必覺得這個房子就是好,未必照樣去造這個房子,但至少大家能看到農(nóng)村房子還可以這么做。
原來村里的工匠想的都是要么根據(jù)開發(fā)商的方式改,要么跟著包工頭做一些改良,其實這些都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下而上就意味著一種百花齊放的狀態(tài)。所以說現(xiàn)在這個社會已經(jīng)沒有固定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了,多元化一定是必然的趨勢。我們把一些很現(xiàn)代的房子放在村子里,反而獲得了一種合法的地位,它被學(xué)習(xí)、被接納,農(nóng)村的生活方式也有了改變,這樣挺好的。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