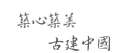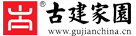成為世遺的良渚,越來越國際范。
可以說,良渚為國際學界認識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多樣性和相似性,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申遺成功后,2019年12月16日,指出“良渚是東亞最早的國家形態”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第三次來到良渚,講座的題目是這樣的:世界史前史中的良渚。
還有一位北大女教授,近20年來直接參與良渚文化的眾多課題研究,年代學、動植物,還有玉石器等等,用良管委副主任蔣衛東的話來說,屬于“驚濤駭浪”、“多面手”。她還是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咨詢專家,參與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文本的撰寫,國際評估專家在良渚現場考察時,她負責學術對話,對世界文化遺產的認知,有著深度見解。
秦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7月1日,我和正在英國的她,在線上聊了聊。后申遺時代,國際學術界如何看待良渚文明;普通人怎樣才能親近這處世界文化遺產。她站在更廣闊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觀點。
記者:良渚申遺成功,公眾或許更關注自身的“意義”——申遺對我們的生活,對這座城市,有什么改變?有什么意義?
秦嶺:申遺的過程和社會影響,遠遠超過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宣傳實施力度,是推進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化遺產保護與當代社會發展相互關系的一個很好的契機;也是促進完善執法和監督機制促進地方政府切實重視遺產保護的一個重要推力。
盡管我們已經有《文物法》和很多地方法規,但不可否認“國保單位”的約束力是遠遠不能同“世遺”相比的。即便如此,世遺委員會在評估過程中,仍然是以本國本地區保護措施相應法規是否完善為依據,這個評估過程本身是推動遺產保護進一步完善落實的過程。
比如良渚申遺在中期報告階段(2019年初),世遺委員會提出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高壩低壩區列入第八批國保的時間表。當然,2019年底,鯉魚山-老虎嶺水壩遺址毫無懸念列入了第八批國保單位,包括江蘇的蔣莊、寺墩也同期列入了第八批國保,這都跟良渚申遺多少有直接間接關系。
對世界上很多地區而言,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是提高知名度、產生附加價值(旅游資源)的有效手段。哪怕是浙江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具體到余杭、到瓶窯,申遺成功無疑提升了區域影響力和本區域的附加價值的。作為遺產地的直接“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在地社區居民和地方政府職能部門都是獲益方,這種收益長遠會體現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短期收益則包括環境改善、就業/創業機會增加、生活品質提高等各方面。(跟瓶窯同名的平遙古城,就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
文化,本質上是人類社會面對所有問題時最終的出路和解決方案,而在文化這個寬泛的概念當中,歷史與藝術,從來都是最有力量并且最容易被共情被認同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申遺表面上是一個在往外推送的事情,內核卻是一個自我賦能(empowerment)的過程。換句話說,從西湖、大運河再到良渚,一次次的申遺成功對杭州人的自我定位肯定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當然,目前對世遺名單的現實意義,有很多討論和不同意見。特別是西方很多發達國家,一方面積極呼吁并投入很多資金和資源開展戰亂或自然災害地區的遺產保護工作;另一方面,當遺產保護(特別是所謂真實性完整性的標準)和自身社會發展產生矛盾時,則往往會進一步反思甚至質疑目前這種遺產保護理念和標準。
比如,德國德累斯頓市18公里長的易北河谷,通過全民公投決定為了緩解內城交通問題便民造橋,2009年因興建森林宮大橋破壞遺產景觀的原因被世遺組織除名。最近,英國利物浦寧愿選擇城市發展,在碼頭區開始大型的城市規劃項目,使得世遺委員會2012年將其列入瀕危名單;去年,埃弗頓俱樂部又官宣了直接在碼頭修建新足球場的規劃,以至于世遺委員會給出最后通牒,本來今年七月福州的世遺大會就要面對是否除名的風險。
歐洲出現的這些現象,是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必須面對的新問題,所謂文化遺產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文化資產”,所以“申遺有什么用”這個問題,在不同社會發展狀況下是會有不同答案的。
記者:20世紀,考古學家和社會公眾常常拿城市、文字、青銅器等幾個教條式標準來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進入文明階段,但近二三十年來大量國內外的考古成果顯示這樣的判斷標準過于簡單粗暴。您此前提到過,良渚古城遺址申遺的過程,對我們,和對西方標準下訓練出來的聯合國專家一樣,都是一種挑戰。具體說說,這是一種什么挑戰?
秦嶺:嗯,說是“教條式”標準、過于簡單粗暴……這種說法我肯定都覺得不妥當的。因為civilization這個詞本身就有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學術原因。對于文明的考古學定義,主要是基于兩河流域早期文明的特點提出來的,并在同舊大陸其他古文明的比較研究下進一步歸納出文字書寫系統、冶金術、城市、社會分化等等一些特征。但說起來,瑪雅人沒有冶金術還在新石器時代;印加人沒有書寫系統還在結繩記事——這些都是西方學術界稱為“文明”的古代社會。所以不是“簡單粗暴說西方定義只有青銅器文字和城市”。
我所說的“挑戰”,在選擇相似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行比較分析之前,我們對良渚古城遺址的特殊性質進行過反復評估:一方面,沒有文字和青銅技術,良渚古城毫無疑問被定義為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產,需要同新石器時代其他世界遺產進行比較,但這樣比,我們良渚就太“高級”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現出來的社會和物質文化發展程度,又無疑是屬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納入城市文明的范圍內,與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進行比較,但后者絕大多數是已經產生了文字的青銅社會,外國學者在不了解材料的情況下,會覺得毫無可比性。
正是隨著良渚古城遺址申遺工作的全方位展開和推動,近年來西方學者才得以有機會正視中國新石器晚期考古的豐碩成果,才會評價說“中國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文明起源發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銅器、城市這樣的西方標準。
再補充一點,對西方學界而言,真正被“挑戰”的不是定義,而是對歐亞大陸早期社會發展進程的理論性認識。上面提到的冶金術、書寫系統、城市等等,是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古埃及等等地區社會復雜化進程中出現的主要變化和階段性特征。因此,西方一直以來把殷墟作為可資比較的“商文明”的代表就可以理解了,這種“平行發展/進化(paralleldevelopment/evolution)”模式是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甚至物種進化的基礎,是一種方法論。
而中國考古學對這種理論和方法論的挑戰,在于不僅僅是一個良渚文明,而是包括并不限于石峁、陶寺、石家河、山東龍山文化等等各種不同形態的新石器時代區域文明,有各自不同的產生背景和社會形態特征,同時又都是在新石器時代作物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為認識理解我們人類社會發展的多樣性和相似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依據。
其實,我們中國的考古學家也是在被新發現不斷推著走的,怎樣算是邁進了文明的門檻?文明探源從什么時候開始探起?最早的中國、最初的中國還是早期中國?每個研究者基于同樣的物質資料都會提出不同的理論性認識,比如二里頭文化和“夏文化”的議題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同樣,良渚到底有沒有文字書寫系統,陶罐上、莊橋墳石鉞上的是刻劃符號還是原始文字——大家也都還有不同意見。所以,所謂“挑戰”西方理論,其實是資料積累促使大家不斷完善和修正的過程,學界的認識和共識都是在不斷變化中的。
記者:良渚古城是我國第一個成為世遺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是否在世界遺產的價值體系中很特殊?
秦嶺:本身《世界遺產名錄》當中,考古遺址這類就已經很少了,加上其他地區出現在名錄上的新石器遺址可視性相對來說都很強(比如巨石陣、比如CatalHoyuk等等),所以良渚能申遺成功還是挺特殊的。
我記不清是陳同濱所長還是誰講到過,它的特殊性也體現在這是一個完全靠考古學家發掘和研究才闡釋了遺產價值的例子。申遺成功時看直播,我也在票圈評論過,當時有突尼斯代表團發言,就明確提到良渚古城遺址之所以能夠獲得提名,是經過科學考古研究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成果入選的典范——可見良渚申遺成功對推動考古研究成為遺產工作核心內容是有世界性的借鑒作用的。
記者:申遺成功后,你所接觸到的國外學者對良渚文明對于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意義,又是怎么看的?是否因為良渚,對中國有了新的了解?尤其是這一年以來,國際上是否有一些新觀點,新研究?
秦嶺:研究東亞地區的專家本來就知道良渚,也跟進最新的研究進展。不做東亞的,實話說并不會因為良渚的出現影響或改變對他們自己研究對象的認識。
良渚文明對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意義,主要還是會通過中國學者特別是該地區考古學家們的深入細致的研究進一步得到揭示。世界范圍內,只有從事比較研究、特別是早期國家/文明比較研究的這些學者,會因為知道了良渚有比較大的觸動,英國劍橋大學的科林·倫福儒教授就是這樣。
記者:對于良渚文化的認識,80年來不斷在變化,不斷在增多,考古學家發現得越多,問題也就越多,以至于我們現在對它的認識,依然可能并不多(以前曾有老師說大概依然不超過20%)。考古不斷接近歷史,但永遠無法完全揭示歷史。這反而更有趣,給了我們很多開腦洞的機會。良渚還有哪些未解之謎,還沒有發現的部分(潛力),是您特別感興趣的?
秦嶺:20%?這個怎么算出來的呀?對于古代社會,我們都無法知道面對的全體是多少,又怎么可能計算出來我們已經知道了多少呢?何況我們認為我們已經知道的不一定是歷史真實(比如良渚有沒有文字)。
從我的專業來講,最小的未解之謎,舉一個例子。比如良渚的石犁到底如何使用,犁耕的話用的是人力還是畜力,這個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有賴以后碰到好遺址。
再從大的角度舉一個例子的話。我認為良渚社會的變革和衰亡都跟玉料資源枯竭有一定關系,但真正造成社會衰退的原因和機制還是很復雜的,再有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積累之后,我們的認識肯定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記者:您這兩年對于良渚文化的關注點在哪里?是否有新的研究課題了?
秦嶺:一個是北大團隊這幾年同江浙皖同行一直合作開展玉器無損分析。主要想通過玉器成分的大數據積累和出土背景的整合分析,來進一步討論良渚文化玉器手工業的具體形態以及獲取玉器這種特殊社會資源的方式和機制。
另一個,最近同我們學院年代學實驗室的老師合作,想利用長江下游地區飽水環境的特點,做樹輪年代學方面的嘗試。由于良渚中晚期階段正好處于樹輪校正曲線的平臺期,大量數據校正后落在一個比較大的年代區間內,要利用碳十四測年數據來分析討論良渚中晚期具體的社會變化節點就很困難。希望結合本地區木材木器的樹輪測年將來能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良渚古城遺址,是完全依靠科學考古發掘出來的一個早期國家,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家80多年持續的工作,我們根本不知道5000年前中國還有一個良渚,我們也不會知道,它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不僅僅是曙光。我認為,良渚也可以成為人們認識考古這門科學的典型案例——公眾對考古的認識一直處于模糊狀態,要么獵奇,要么消費。在您看來,良渚突出普遍價值的陳述中,良渚的考古發掘占據怎樣的地位和作用?在良渚遺址申遺的過程中,考古學又如何參與遺產保護工作?
秦嶺:OUV(突出普遍價值)是對遺產價值的總結,并不直接體現考古發掘的作用。但就像你說的,不挖就沒有良渚文化了,還談什么突出普遍價值呢?
良渚申遺本身,也是考古學家對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內涵不斷學習的過程,通過這個申遺過程,也有助于考古學工作者更清晰今后的發掘研究工作同遺產保護的關系。
我個人覺得這個關系可以分幾個層次:第一,需要通過考古學發掘研究來確認和保障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第二,需要通過考古學發掘研究來揭示和論證遺產的本體價值;第三,考古遺址的管理保護和規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考古學發掘研究成果才是有效開展遺產保護工作的核心依據。
總之,像良渚古城這樣的考古遺址類的文化遺產,考古絕不是為了編制規劃、為了申遺提供素材的,它應該是今后遺產管理保護中有序開展的一項核心工作。
記者:良渚申遺成功后,對我們有哪些啟發?
秦嶺:我記得去年申遺剛剛成功時,大家都談論和總結過申遺成功的原因。實質上,成功的種種原因本身就給我們很好的啟發和示范作用,當然這種作用的目標是要繼續“復制”成功。事實也是如此,去年陜西石峁遺址被正式提出要列入中國的遺產預備名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良渚申遺成功不僅是提升了大家對良渚本身的關注度,也增強了其他考古遺址“復制成功”的期望值。
就申遺這項工作而言,良渚古城遺址的成功經驗,其核心我想應該還是本地區考古學家們幾十年來的工作積累和堅持不懈的科學探索,這個世界文化遺產是靠他們一代代人一點點“挖”出來的,這點毋庸置疑。這也給了當下遺產管理保護工作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任何遺產工作都需要以遺產研究為基礎、為核心、為依據。
在人口密度高、耕地面積大、經濟發展快速的現代中國,考古遺址尤其具有脆弱性。不同于歷史建筑/紀念碑等可視性強的文化遺產,對考古遺址完整性的破壞往往不會那么直觀直接,也因此更容易“悔之晚矣”。
我想說申遺成功的第二個啟發,就是希望各級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能由此意識到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才是管理保護工作的重點和難點。遺產保護和地方建設的矛盾中,承擔“遺產看守人”責任、發揮“遺產管理者”作用的應該是地方政府。考古工作者的職責是通過我們的科學工作給予規劃決策部門有關遺產價值和內涵的全面評估,并不是去做一只到處呼吁和擋車的“螳螂”。
最后,史前考古遺址本身是一個特定時段內文化和社會的綜合體,其價值是多面也是多義的,因此需要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聲音,更需要在與當代社會的互動中得到觀照產生回響。良渚申遺成功后,這短短一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基于良渚的藝術創作,文創產品和文化活動,這幾天票圈又在熱議央行馬上要發行的金銀紀念幣。關于良渚的文本也不再僅僅是考古報告和學術論文,比如您馬上要出版的大作,各類童書,各種公眾號的推送等,閱讀和實踐的主體正在不斷擴展,遠遠超出學術研究群體力之所及。
所以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啟發就是,申遺成功使良渚走出了象牙塔,也走出了考古,如何去實踐和實現“人民群眾是文化遺產真正的主人”?——最后這個問題,我想是所有人都可以來回答的。
記者:接您的回答,說到和我們每個人有關系的事,普通人如何走近良渚?要了解這個世界文化遺產,我們必須得來現場看一看,否則很多人是無感的。但來了之后,大家普遍發現一個問題。我們去良渚古城遺址公園,空曠無垠,美則美矣,但少了一點畫面感——人們習慣了西方紀念碑式的物質文化,比如大型神廟建筑,宏偉,有感覺。但我們在良渚看到的是“地上土丘一片”,我們的城墻、宮殿,是地下土遺址,很多人逛完公園,認為“看不懂”。從一個游客的角度,您覺得我們到遺址公園,應該看什么,怎么看,才能所謂“看懂”——從我的角度看,去良渚遺址公園,最大的感受應該是——感受,但大部分人會想來這里直接看懂良渚。
秦嶺: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良渚古城遺址”,本身是由四個要素構成,分別為“城址”、“瑤山遺址”、“谷口高壩區”和“平原低壩與山前長堤區”。目前,就我的了解,大部分觀眾可能就是博物院加古城遺址公園這樣的參觀路線,其實并沒有看全咱們這個世界文化遺產。正如你說的,所謂“看懂”,應該是“感受”,而這個感受,很重要的一點是需要通過空間距離和遺跡的體量來充分體現。
如果大家能從莫角山出發爬上瑤山,切實體會到這個距離感(通過騎行或步行的感受可能更容易與古代人共情),“感受”到瑤山墓地突出的規劃性。同時,能從古城出發沿路通過塘山、低壩和高壩區來“感受”所謂大型水管理系統的存在,特別是歷時五千年仍然同“苕溪大堤”一樣是當下景觀的一部分。這種體驗感,可能比坐電瓶車在公園里面兜一圈會更為深刻。
另一方面,“感受”是需要“穿越”的。
目前,北大正在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良管委商議開展各類實驗考古的具體事項。如果沒有這場疫情,這個暑假,來古城遺址的觀眾或許就可以看到我們正在蓋房子做玉器了。在沒有金屬工具的前提下,手工雕琢硬度很高的透閃石——如果你能親自體驗或者觀察到這個過程,再回過去看博物院里規整的良渚玉器和上面精細的紋飾,“感受”肯定是會不同的。
同樣,在沒有機械裝置和現代工具的前提下,利用河道來搬運木材,只能用石質工具來挖槽筑墻蓋房子——這種“感受”,跟現在爬到莫角山頂上看仿真木柱和地上不同顏色的長方形肯定也是效果不同。
我們去瞻仰古跡想要獲得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這是遺址公園在規劃設計時需要為觀眾考慮的。正如你說的,美則美矣,但好像少了點什么——缺少的這個,是我們仰視金字塔時、或者屏息進入莫高窟時所產生的對歷史對人類文明成就的敬畏感。正是這種時間上的距離感和物質上的真實性,共同構成了文化遺產不可替代的價值。一座仿古建筑或一件復制品是無法給予這種“感受”的,而考古遺址公園的挑戰,就在于如何復原才能實現這種真實。從這個角度講,良渚古城申遺成功才只是一個開始,如何使它真正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才是接下來的挑戰。
記者:很多人對良渚文化、良渚文明,這兩個概念一直搞不太清楚,但人們其實又對“良渚文明”——文明模式,非常感興趣。良渚文化為什么可以上升到良渚文明?
秦嶺:良渚文化是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最初柴爾德的定義是“一批總是反復共生的遺存類型――陶器、工具、裝飾品、葬俗和居址形態”。
中國學術語境下最有代表性的定義,比如嚴文明先生的“專指存在于一定時期、一定地域、具有一定特征的實物遺存的總和”,他同時也說考古學文化是有層次性的,包括分期分區分類型等等。對比仰韶、龍山文化這樣內涵和定義相對寬泛且復雜的情況,再對比很多新發現、新命名,因此學界未有共識的情況(本地就有錢山漾-廣富林、上山-小黃山、跨湖橋-井頭山這樣的例子),良渚文化可以說是一個時空范圍和物質文化特征都非常明確的考古學文化,沒啥爭議之處。
良渚文明,是對這個時期古代社會發展狀況的一個理論性認識,就是說學界認為良渚文化階段環太湖地區的這個史前社會已經發展到可以稱為“文明”的這樣一種社會狀況。早期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不一定是線性或者持續有方向的。
比如,我們不可能稱上山文化為“上山文明”;同樣良渚文化之后,我們也不可能繼續說“錢山漾文明”或者“馬橋文明”。這樣講是不是比較容易理解?
“文明”是對社會結構和發展狀況的一個理論性的描述,這其中最主要的衡量標準就是社會的復雜化程度。而良渚文化的物質文化特征顯示,從資源分配、經濟分工、社會分化以及早期信仰體系的統一性等各方面綜合考慮,這個階段的社會復雜化程度都無疑可以稱為“文明”。
良渚文明是怎樣一種文明?用世遺委員會的表述就可以,它是“一個新石器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至于它的代表性,世遺說的是“通過大型土臺建筑、城市規劃、水利系統以及墓葬墓地差異所體現的社會等級制度,使該遺址成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Theseruinsareanoutstandingexampleofearlyurbancivilizationexpressedinearthenmonuments,urbanplanning,awaterconservationsystemandasocialhierarchyexpressedindifferentiatedburialsincemeterieswithintheproperty)”,這就很清楚,是說明它的發展程度和區域特點了。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