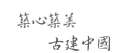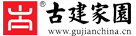孫機(jī),1929年生,山東青島人。文物學(xué)家。1949年,進(jìn)入華北軍政大學(xué)學(xué)習(xí),后到北京市總工會(huì)工作。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專業(yè),1960年畢業(yè)后留系工作,1979年到中國(guó)歷史博物館(今國(guó)家博物館)考古部工作。現(xiàn)為國(guó)家博物館終身研究館員,國(guó)博研究院名譽(yù)院長(zhǎng),國(guó)家文物鑒定委員會(huì)副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著有《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中國(guó)古輿服論叢》《仰觀集》《中國(guó)圣火》《從歷史中醒來(lái)》《中國(guó)古代物質(zhì)文化》等。
今年國(guó)慶節(jié),孫機(jī)先生的《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修定本)》即將由中華書(shū)局付梓,我去拜訪他。老先生高興地談起不久前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shí)發(fā)表的關(guān)于考古工作的講話,還拿出不久前的《光明日?qǐng)?bào)》讀給我:“我們要加強(qiáng)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chǎn)、書(shū)寫(xiě)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lái),豐富全社會(huì)歷史文化滋養(yǎng)。”
“這話說(shuō)得太深刻、太精準(zhǔn)了!”孫機(jī)先生說(shuō),不僅要把我國(guó)的考古發(fā)現(xiàn)研究透,而且要讓古代的社會(huì)生活活起來(lái),這里面包含著文化自信,加強(qiáng)文化自信的目的是加強(qiáng)愛(ài)國(guó)主義,增強(qiáng)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我們考古工作者肩負(fù)著這么一個(gè)任務(wù)。”
要由小見(jiàn)小,也要由小見(jiàn)大
年輕時(shí),孫機(jī)曾想寫(xiě)一本書(shū),書(shū)名就叫《物源》。那時(shí),他的學(xué)術(shù)興趣是探究事物的來(lái)歷,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態(tài)的東西,究竟從何而來(lái),會(huì)向何處發(fā)展。回想幾十年的學(xué)術(shù)之路,雖然沒(méi)有寫(xiě)出一部名為《物源》的著作,但孫機(jī)的研究一直與“物源”息息相關(guān),他也一直保持著最初的那份念想。
這些年來(lái),各地出土了很多文物,有些盆、罐、瓶,人們一看就明白,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也有些東西,學(xué)界一直不知道它們是做什么用的。文物能夠?yàn)槟莻€(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生活提供注解,但有些古代的東西沒(méi)有流傳下來(lái),慢慢被湮沒(méi)在歷史里,今天的人們已經(jīng)不了解它們的用途,就有必要探索“物源”。他舉了兩個(gè)例子,一個(gè)是霞帔墜子,一個(gè)是三子釵。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霞帔墜子,剛出來(lái)的時(shí)候,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圖片發(fā)表時(shí),尖朝下,有人認(rèn)為是香囊、銀熏或佩飾。對(duì)照明代典籍就可以知道,這個(gè)東西叫霞帔墜子,應(yīng)該尖朝上。霞帔是從肩膀上垂下來(lái)的飄帶,帔底下就是個(gè)墜子。追溯起源,霞帔在唐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經(jīng)過(guò)唐宋的發(fā)展,到明代,霞帔及墜子的佩戴規(guī)定已經(jīng)嚴(yán)格:一品至五品的官員,霞帔上墜金帔墜;六品、七品,綴鍍金帔墜;八品、九品,綴銀帔墜。霞帔墜子這個(gè)小物件的變化,反映了中國(guó)輿服制度的一個(gè)側(cè)面。
三子釵的辨識(shí)也很有意思。三子釵多為銅制,一般長(zhǎng)15~17厘米,當(dāng)中為長(zhǎng)條形橫框,兩端為對(duì)稱的三叉形;有些出土文物,居中的一股再分為兩叉,且與兩側(cè)的兩股分別彎成三個(gè)呈品字形排列的不封閉的弧圈。最開(kāi)始有人把這認(rèn)作擱筆的支架等物,后來(lái)在一具未被攪動(dòng)的女性頭骨上端出現(xiàn)此物,才給人啟示,這可能是婦女用的發(fā)飾。
講到這里,孫機(jī)拿出他的舊作《從歷史中醒來(lái)》,翻到山東臨沂西張官莊出土的漢畫(huà)像石上的女神像,頭上清清楚楚地戴著這種發(fā)飾,“這樣我們就可以確認(rèn)無(wú)疑這是一種發(fā)飾,但是叫什么名字呢?這就需要到文獻(xiàn)中去找答案。根據(jù)文獻(xiàn)記載,這個(gè)物件是三子釵,又名三珠釵”。
孫機(jī)說(shuō),這些只是“由小見(jiàn)小”的例子。霞帔墜子也好,三子釵也好,都是些小物件,把它們說(shuō)清楚了,也只是說(shuō)清楚了一個(gè)裝飾品或者一件小事。研究古代文物,不僅要“由小見(jiàn)小”,而且要“由小見(jiàn)大”。一件東西說(shuō)清楚了以后,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生活的很多方面可能都會(huì)有新的認(rèn)識(shí)。這樣的例子也有很多。
比方說(shuō),西漢初年社會(huì)上普遍譴責(zé)秦始皇的暴政。在秦始皇的諸多暴政當(dāng)中,有一個(gè)叫“頭會(huì)箕斂”,是說(shuō)秦軍拿著一個(gè)像簸箕一樣的東西去老百姓家隨意斂收糧食,供給軍費(fèi),遭到老百姓的抱怨。前些年學(xué)者在山東博物館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銅箕,上面鑄著秦始皇統(tǒng)一度量衡的詔書(shū),證明這是個(gè)量器。從秦往下,到漢朝,雖然沒(méi)有發(fā)現(xiàn)這類實(shí)物,但是發(fā)現(xiàn)了它的模型,就是出土的一套量具,跟斗、升等一塊兒,還有一個(gè)箕,那么這個(gè)箕就是一個(gè)量具。從秦往上,戰(zhàn)國(guó)甚至商代都有這種量具。所以說(shuō),中國(guó)古代量器當(dāng)中有箕量,文獻(xiàn)上也這么說(shuō)了。這樣的話,不管老百姓怎么抱怨秦暴政把收糧食的比例定得高,但是不可能說(shuō)拿著簸箕隨便就裝,裝完就走,那就不是政府行為了。所以,這個(gè)“頭會(huì)箕斂”就是當(dāng)時(shí)漢初的人譴責(zé)秦朝的時(shí)候說(shuō)得比較夸張的一句話。出了這個(gè)箕量以后,事情就可以搞清楚了。
通過(guò)這件文物可以把秦朝賦稅制度說(shuō)得更清楚。這個(gè)東西的發(fā)現(xiàn)就是對(duì)文獻(xiàn)的一個(gè)補(bǔ)充說(shuō)明,也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整個(gè)社會(huì)狀況的一個(gè)說(shuō)明,它這個(gè)是“由小見(jiàn)大”的例子。
孫機(jī)又舉了個(gè)例子,是寧夏固原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棺。這個(gè)漆棺上畫(huà)的是中原的二十四孝圖,但人物都穿著鮮卑裝,兩種文化都有體現(xiàn)。孝文帝改革以后,不僅改穿漢服,而且把籍貫都改了。原本他是今天大同那一帶的人,籍貫改成了洛陽(yáng),而且不許再說(shuō)本民族的鮮卑話,引起了舊貴族的反感,導(dǎo)致他的親兒子都反對(duì)他,后來(lái)就反叛了。固原漆棺畫(huà)早于孝文帝改革,使我們對(duì)這次改革的背景有了更多了解,從而對(duì)改革的全過(guò)程得到一個(gè)較為完整的印象。
讓古代的社會(huì)活起來(lái)
全盤(pán)整理五千年的中華文化遺產(chǎn),目前還很有難度,尤其唐代以后的文獻(xiàn)浩如煙海,想要窮盡幾無(wú)可能,但整理一個(gè)朝代還是有可能的。孫機(jī)選擇了以漢代作為橫切面,先讓一個(gè)朝代“活起來(lái)”。他的嘗試,主要就體現(xiàn)在《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里。
漢承秦制,是中國(guó)歷史上第二個(gè)統(tǒng)一王朝,歷時(shí)400多年。從國(guó)家層面而言,其制度、文化、社會(huì)等方面相對(duì)成熟,可以作為一個(gè)橫斷面去研究,而且漢代的文獻(xiàn)相對(duì)有限,下點(diǎn)功夫,可以將現(xiàn)存的漢代文獻(xiàn)通讀。再者,漢代文物層出不窮,可以與文獻(xiàn)相互印證、互為表里。投身漢代文物與文獻(xiàn)的世界,就有如走進(jìn)一條可以歷覽漢代眾生相的大畫(huà)廊。
孫機(jī)的中國(guó)古代的物質(zhì)文化研究,既包括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等生產(chǎn)內(nèi)容,也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內(nèi)容。在《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這本書(shū)里,孫機(jī)把漢代生產(chǎn)、生活等方面的事物,分成了100多個(gè)小題目,衣、食、住、行,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冶金、采礦等生產(chǎn)生活方面都包括在內(nèi)。
對(duì)這些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的每一個(gè)方面,孫機(jī)都會(huì)從基礎(chǔ)講起,細(xì)致梳理源流。比如,紡織方面,先講桑、麻、蠶絲等原材料,然后講紡織用的各種機(jī)具,再講由這些原材料織成的面料——錦、帛等,然后講刺繡、染色、印染等手段,進(jìn)而介紹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樣的紡織品。講完紡織之后,就講衣服,怎么剪裁、怎么穿,再講首飾及其他。又比如,農(nóng)業(yè)從耕地說(shuō)起,然后說(shuō)播種、灌溉、五谷等。看了這本書(shū)的人,就能從根兒上對(duì)這些知識(shí)有所了解。
“過(guò)去,有的國(guó)家把考古研究所叫物質(zhì)文化研究所,這就是說(shuō),考古研究的主要對(duì)象是具體的物質(zhì)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還有的國(guó)家,把考古學(xué)科放在人類學(xué)里,主要側(cè)重于史前史,就是人類進(jìn)入文明以前,沒(méi)有文字的時(shí)代。做這個(gè)時(shí)代的研究,只能采取層位學(xué)、類型學(xué)的方法對(duì)具體的物質(zhì)進(jìn)行研究。人家說(shuō)蘇秉琦先生閉著眼睛摸陶器的口沿,就能知道它是早是晚,因?yàn)樗麑?duì)類型學(xué)太熟悉了。但考古學(xué)在確定文物的年代之后,還要復(fù)原社會(huì)面貌。史前時(shí)代沒(méi)有文字記載,復(fù)原這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面貌,讓它活起來(lái),是很不容易的。”孫機(jī)說(shuō),通盤(pán)看中國(guó)歷史,堯舜以前的歷史比較渺茫,三代以后就比較具體了,有文字以后的歷史是重點(diǎn),通過(guò)實(shí)物和文獻(xiàn)記載相結(jié)合,對(duì)事物的認(rèn)知就會(huì)具象很多。
實(shí)物和文獻(xiàn)記載結(jié)合,是孫機(jī)從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方法。王國(guó)維提出二重證據(jù)法,是指考古的文獻(xiàn)和傳世的文獻(xiàn)相印證。現(xiàn)在的二重證據(jù),是要將實(shí)物和文獻(xiàn)相結(jié)合,這樣就能把歷史事件解釋得更活了。這些更活的材料,就不僅是二十四史、十三經(jīng)這些傳世材料,還有考古發(fā)掘的古代話本、文書(shū)等各類文獻(xiàn)。不管是傳世文獻(xiàn)還是出土文獻(xiàn),只要是真的、可靠的,與器物研究有關(guān)系,就可以不拘一格,拿來(lái)互相對(duì)照,擴(kuò)大印證的范圍,使古器物和古文獻(xiàn)“打成一片”。
呈現(xiàn)中華文明對(duì)世界的貢獻(xiàn)
孫機(jī)專注于漢代物質(zhì)文化研究,已經(jīng)有四十年了。他說(shuō),今年這本《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修定本)》出版后,以后不會(huì)再有機(jī)會(huì)修改了,所以叫“修定本”。這是他最看重的學(xué)術(shù)成果。
從橫斷面來(lái)說(shuō),孫機(jī)的研究考察了漢代基本物質(zhì)文化資料,從縱向來(lái)說(shuō),貫穿整個(gè)中國(guó)古代。但是他謙遜地認(rèn)為,即便如此,自己仍沒(méi)有能力將各個(gè)斷代的物質(zhì)文化都以像《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那樣的方式研究出來(lái),其他時(shí)代的研究只能有待來(lái)者,“考古工作不只是‘由小見(jiàn)小’‘由小見(jiàn)大’,或者考古和文獻(xiàn)相結(jié)合,還要通過(guò)對(duì)考古成果的研究,認(rèn)識(shí)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這就不是理清幾件文物的名稱和用途的問(wèn)題,攤子還要鋪得更大”。
在他看來(lái),研究古代物質(zhì)文化,不僅能讓人們更加了解、熱愛(ài)祖國(guó)的歷史,而且能為今天的建設(shè)提供動(dòng)力,“我們說(shuō)考古對(duì)社會(huì)有用,不是說(shuō)考古能為今天的社會(huì)生活直接提供一個(gè)什么新技術(shù),而是說(shuō)考古可以增加文化自信,進(jìn)而加強(qiáng)愛(ài)國(guó)主義”。
17世紀(jì)歐洲工業(yè)革命以前,中華文明在很多領(lǐng)域領(lǐng)先世界其他國(guó)家。有學(xué)者研究,到了清朝乾隆時(shí)期,中國(guó)的GDP還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原來(lái)只說(shuō)中國(guó)有“四大發(fā)明”,其實(shí),中國(guó)有很多發(fā)明創(chuàng)造影響了世界。英國(guó)學(xué)者李約瑟就指出,中國(guó)有70項(xiàng)發(fā)明曾經(jīng)領(lǐng)先世界,后來(lái)傳到了歐洲。
前些年,有學(xué)者提出,中國(guó)的馬車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孫機(jī)對(duì)古車做了大量研究后認(rèn)為,中國(guó)古車與西方古車完全是兩個(gè)體系,差別極大:從構(gòu)造上說(shuō),有大輪、小輪之別;從系駕法上說(shuō),有軛靷式系駕法和頸帶式系駕法之別;從性能上說(shuō),有用于車戰(zhàn)和用于運(yùn)載之別。距今約3700年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fā)現(xiàn)了雙輪車的轍痕,從考古上證明中國(guó)此時(shí)已經(jīng)有車。《尚書(shū)·甘誓》是夏朝初年夏后啟討伐有扈氏的誓師詞,應(yīng)該是可信的材料。誓詞中對(duì)作戰(zhàn)的具體要求是:“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這段話反映出當(dāng)時(shí)不僅有車,而且能進(jìn)行車戰(zhàn)。一輛車上配備了車左、車右、御手等三名車士,組成一個(gè)戰(zhàn)斗單位。可見(jiàn)此時(shí)戰(zhàn)車兵已經(jīng)有明確分工,車戰(zhàn)戰(zhàn)術(shù)已經(jīng)規(guī)范化。如果所駕馭的不是性能良好的戰(zhàn)車,則不僅不能正常發(fā)揮其戰(zhàn)斗力,也積累不起足以上升為軍事條令的戰(zhàn)斗經(jīng)驗(yàn)。中國(guó)馬車出現(xiàn)的年代與中亞、西亞馬車出現(xiàn)的年代相仿,并不存在西方已有了成熟的車型而中國(guó)緊隨其后的情況。
從系駕法方面考察,中國(guó)古車與西方古車大相徑庭。系駕法是將牲畜拴在車上,使之充分發(fā)揮拉車的能力,易于接受操控。1980年在陜西臨潼秦始皇陵封土西側(cè)出土了兩輛銅車馬,全副挽具包括像繁纓這類細(xì)節(jié),都用金屬逼真地復(fù)制了出來(lái),中國(guó)古代的系駕方法從而表現(xiàn)得清清楚楚。這輛車由兩匹服馬所負(fù)之軛的軥上各引出一條靷繩來(lái)拉車,而且在軛肢外側(cè)還附上加固桿,證明這里確系拉車的主要受力之處。兩靷的后端系在輿前的環(huán)上,再用一條粗繩將此環(huán)與軸的中心縛結(jié)。拉車時(shí),馬肩胛前的軛受力,兩靷傳力,完全不影響馬的呼吸,這就是“軛靷式系駕法”。再拿它與商周車馬坑出土的遺物相印證,可知中國(guó)先秦古車的系駕法實(shí)為一脈相承,前后并無(wú)二致。
西方則不然,那里的古車是用頸帶將牲畜的頸部固定在衡上,牲畜拉車時(shí)由于頸部受力,通過(guò)衡和轅拽動(dòng)車子前進(jìn),被稱為“頸帶式系駕法”。由于頸帶壓迫牲畜的氣管,牲畜跑得越快呼吸越困難。無(wú)可辯駁的史實(shí)是,到公元8世紀(jì),歐洲的馬車才放棄了頸帶式系駕法。
孫機(jī)又舉了球墨鑄鐵的例子,1947年,歐洲的冶金專家才研究出現(xiàn)代的球墨鑄鐵技術(shù)。球墨鑄鐵比一般的鑄鐵強(qiáng)度更為增加,機(jī)械性能也更為改善。讓人驚訝的是,在河南鞏義鐵生溝冶鐵遺址出土的西漢鐵器里,就檢驗(yàn)出發(fā)育良好的球狀石墨,它的球化率甚至符合現(xiàn)在的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雖然那個(gè)時(shí)候的球墨鑄鐵工藝還不成熟,但對(duì)我們總有一些借鑒意義。
它雖然不跟現(xiàn)在連接,但把它的古代社會(huì)就搞活了。活了以后我們就看到古代社會(huì),那么有秩序,不是那么亂,而且技術(shù)又那么發(fā)達(dá),很多文明我們都處在世界前列。
考古不只是往后看
1955年,孫機(jī)考入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從那時(shí)起,他就開(kāi)始研究中國(guó)古代物質(zhì)文化。在北大,孫機(jī)最親近的老師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告訴他,考古研究要多讀書(shū),而且要讀有用的書(shū),讀的時(shí)候特別要注意物質(zhì)文化方面的史料,史料里會(huì)有很多“觸角”,這些“觸角”會(huì)觸及方方面面,有些東西就會(huì)互相聯(lián)系起來(lái),成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入口。
宿白先生1957年發(fā)表的考古報(bào)告《白沙宋墓》,讓孫機(jī)印象深刻。這本書(shū)不僅把壁畫(huà)中反映的歷史說(shuō)得很清楚,而且文字生動(dòng),書(shū)中引用的文獻(xiàn)大多是第一手材料和最好的版本。在他看來(lái),這與宿白先生原來(lái)在北大圖書(shū)館做過(guò)事有關(guān)。孫機(jī)一直謹(jǐn)記宿白先生的教誨,在北大學(xué)習(xí)和工作期間,也常常利用北大圖書(shū)館豐富的藏書(shū)。雖然讀書(shū)很少有直接的發(fā)現(xiàn),但讀得多了,把各種書(shū)聯(lián)系起來(lái),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問(wèn)題。如此慢慢積累下來(lái),就打下了做學(xué)問(wèn)的底子。
學(xué)考古的學(xué)生都會(huì)上考古繪圖這門(mén)課,孫機(jī)也受過(guò)這個(gè)訓(xùn)練,而且特別重視。在他的著作里都配有他自己畫(huà)的線描圖。孫機(jī)說(shuō),從年輕時(shí)試寫(xiě)論文開(kāi)始到《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修定本)》,這么多年積累了上千幅古代器物的線描圖。畫(huà)圖不容易,有的時(shí)候,他吃完晚飯就坐下來(lái)開(kāi)始畫(huà),等畫(huà)完了,抬頭一看,天都亮了。現(xiàn)在印刷條件好了,很多考古、文物圖書(shū)都直接采用照片而不用線描圖了。但孫機(jī)認(rèn)為,線描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把要表現(xiàn)的細(xì)節(jié)刻畫(huà)得更清楚。這次出版的《漢代物質(zhì)文化資料圖說(shuō)(修定本)》,有近20幅線描圖因?yàn)樵娴男Ч惶硐耄撬匦庐?huà)的。他覺(jué)得,如果不重新畫(huà),就那樣黑乎乎地印出來(lái),太對(duì)不起讀者了。
如今,“大眾考古”“公眾考古”的說(shuō)法很流行。孫機(jī)說(shuō),“大眾考古”不是讓大家都去考古,而是讓大家了解考古的知識(shí)。地下文物歸全民所有,進(jìn)行發(fā)掘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zhǔn),否則,即便是在自家院子里發(fā)現(xiàn)古墓,也不能任意發(fā)掘。考古學(xué)家是奉政府的命令去挖掘,這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他不為政府工作的話,那就是盜掘了。向大眾普及考古知識(shí),應(yīng)該重在普及考古的成果,而不是普及田野考古的技術(shù)或方法。
今年已經(jīng)91歲的孫機(jī),仍然關(guān)心著當(dāng)下的考古事業(yè)和國(guó)家的發(fā)展。他說(shuō),我們的國(guó)家需要向前看,考古學(xué)不是讓人們往后看,而是讓我們?cè)黾酉蚯暗膭?dòng)力。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