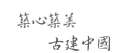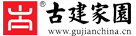在美術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形式的作品,美術作品即包括實用又包括審美,這兩點的比重在不同作品中肯定不同。如果說美術作品的意義主要在于其思想性,那么這樣說也不免有些偏頗,因為許多美術作品主要在于形式美的展現。思想性指什么?應該說是反映社會與社會相掛結,這也應該是畫家的責任。為此如果畫家不具有體察社會的能力和不具有與社會對話的能力的話,他的作品就會與社會主流疏離。不過歷來對作品的實際評價的低昂卻并不完全以所表現的內容為標準,而是根據其作品的筆墨藝術水平。這樣看來,對于一位國畫家來說,他的繪畫作品取悅社會的看點基本是本著其美術性了。
不過應該說美術作品的思想性對于美術作品品質的提升具有巨大的作用,所以這確實應該得到畫家的重視。一件繪畫的品質高低倚賴于思想性和它的藝術性,所以呈現藝術性的造型自然也是很重要的。美術作品自當以美為美。在美術作品中美自然指被表現的物體的外在形式。物體外在形態在不同角度呈現出的美不盡相同,美術家的使命就是將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為此我們可看出思想性屬于作品內在的,它是通過無論美還是不美的作品的外在形態來顯現的。我們這里主要談外在美的作用。
對于社會上的人來說,對基本的形式美的認識還是相差不大的。特別是表現具有一定階級意義的作品,審美者的立場雖然有別,但對于外在形式美的認識還是一致的。比如王式廓的《血衣》,畫中用丑化的形象描寫地主,不但使對立于地主的人會以為這里的地主形象丑,即使親地主的人雖然內心親近地主但在審美上也會認為那形象丑。我們這里如此說的目的是說,對于美術中的形象美丑人們存在著共識,與立場沒有什么關系。弄清了這個問題,我們才好直接品評一切美術作品的美丑問題。
首先,對于形式美的認知人們之間會存在著一定差異,它來自于人以往的生活和審美經驗。比如一幅表現高山峻嶺的山水,它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美的,但對于一個曾經在大山中迷失路徑險些喪命的人來說,看到它就會聯想起那段噩夢般的遭遇,非但不會有美感產生,而且還會感到恐懼。再比如齊白石畫的一幅老鼠偷油圖,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會覺得生動有趣,但如果對于曾遭到老鼠驚嚇的人來說,雖然畫中老鼠的形象已經得到藝術的夸張和美化了,但依然不會感覺到美感來。這就好比人們對蟑螂一樣,因為人們聽到過它帶有大量細菌的宣傳,心中已經留下了陰影,故此很難從審美上來正確的對待它。這種由心理造成的審美障礙在美術審美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它卻可以告誡書畫家在進行創作的時候必須注意回避那些審美麻煩,選擇那些具有普遍迎合意義的內容。不過這樣作并不意味就完全解決了作品審美的問題了。因為作品受歡迎與否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這就涉及到畫家的表現手法和對于美的認識理解了。
另外,對于社會和自然中事物的美丑人們大體的認識還是基本一致的。我們舉文學中的例子來說,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記述的“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無疑這是不美的景象,而“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肯定是美的。以人的形象美丑來說,曹植在《洛神賦》中描繪的洛神是“秾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無疑她是美的。但這種描述不免含混,當我們用顧愷之所繪洛神來驗證時,我們卻有些失望。那么,是不是顧愷之沒有認識到曹植描述的洛神應有的美呢?這可能會有三種情況:一種是顧愷之眼界所及這就是最美的,一種是以他當時的表現技法水平來說只能達到如此,一種是他對美人的認識就是如此。歷史上對仕女美的認識是有些出的入,但并不起源于顧愷之時代。我們可以理解的是顧愷之本意上是力圖將曹植的描述復原,他所繪的是典型的魏晉美女瘦骨清象,氣度高古的風姿。甭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所描繪的洛神即仕女與后代一些畫家描繪的大體還是相同的。
唐有著名的仕女畫家張萱、周昉。周昉筆下的《簪花仕女圖》、《揮扇仕女圖》在造型上注重寫實求真,女子臉型圓潤飽滿,體態豐腴健壯,氣質雍容高貴。張萱流傳下來的作品是《搗練圖》和《虢國夫人游春圖》,女子形象大抵類似周昉。因為此時期對美的認識就如此,所以仕女圖出現了在我們今天看來并不美的形象。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并不是國畫的表現手段不能畫出美,而是取決于畫家對美的認識能力及社會的普遍認同到了哪里美就會出現什么形式。到了宋朝,開始轉變了唐以豐滿為美的審美意識,面龐呈長圓體態向消瘦輕盈發展,如蘇漢臣的《妝靚仕女圖》和劉松年的《天女散花圖》中的仕女一改唐仕女的圓胖臉、體態豐盈。他們表現出的依然是細眉細眼的模樣,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美人。明朝仕女畫基本沿襲了宋的風格,并且自此以后到晚清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格局,直至民國后才逐漸出現了新的仕女形象。比如明唐寅的《孟蜀宮伎圖》、《簪花仕女圖》;另外還有一類寫意式的如《秋風紈扇圖》《牡丹仕女圖》,但面目形態身態基本也如此。明代及明代以后仕女繪畫形成了程式化。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看到仕女的細長眼從現存最古的〈洛神賦〉起,一直到清末民初,一直是細長鳳眼。有研究者認為“仕女圖中千篇一律的單眼皮,在晉朝和唐朝可能出于寫實。然而,宋朝以后,將美人畫成單眼皮卻成為一種程序”。”不錯,這樣的推斷符合宋以后仕女畫得實際。仕女畫的程式化不但把靈活的筆墨表現程式化為勾線、分染、罩染、開臉和復勾,而且它還束縛了畫家的創作空間使之成為千篇一律的復制式模樣,并約束了觀賞者的審美空間,把人們心目中本來千姿萬態的仕女形象濃縮為單一的“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鴨蛋臉”模式,并且大部分仕女圖中的仕女表情也很呆板。
這里我們還必須提及的是,作為國畫作品來說形象美的表露包括兩部分,一是人物形象,一是筆墨的功力。特別是寫意式的人物畫。故此筆墨的書法功力在形式美中占據了決定性作用。有些人物畫盡管人物形象不錯,暈染皴擦也很到位,但如果在用筆的地方書法性很弱的話,則會使美打了不小的折扣。而如果具有堅實的筆墨功底的支撐,則會具有回天的驚人效果。我們下面就證明一下這種現象。
在明末出了個陳老蓮,他的仕女畫對于傳統仕女畫應該說是具有開拓、叛逆意義的。不過遺憾的是他的人物畫用筆古拙,人物形象又以怪誕著名,如果將怪誕創作理念用在表現男子那是沒什么可挑剔的,但如果用在表現年輕漂亮女性上,則顯得有些不倫不類了。因為仕女在人們心目中幾乎就是有身份的高雅年輕漂亮女子的代稱。如果將仕女畫成要相貌沒相貌,要身段沒身段的話也就沒什么美可言了。無論怎么說,這種仕女圖在外在形象上都帶有丑化性質,無疑它的欣賞價值則會大打折扣。我們拈出陳老蓮表現古代仕女形象的兩幅作品(見圖1圖2)。這里無論從身材上還是相貌上都不能令人感覺到有美的含義來。而且我們根據陳老蓮那個時代其它一些畫家筆下的仕女形象(見圖3)來推斷,人們也不會以此形象為美的。
陳老蓮筆下的仕女形象不美,那么他畫的非仕女的人物是否就美了呢?回答是肯定的。那是因為陳老蓮表現出了人物的情感和性格,而且形象怪誕與形象猥瑣有著天壤之別,那是質的區別。我們可以看到支撐陳老蓮仕女圖藝術魅力的核心力量主要在于他古拙的用筆。黃賓虹說:“筆力上紙,能力透紙背,以此作畫,必不膚淺。”陳老蓮就有如此的功力。那么是不是誰都可以運用古拙用筆呢?這里必須說的是,古拙用筆的基礎是書法用筆!就是說,倘若陳老蓮沒有堅挺的書法功力,他的古拙就僅僅會屬于在外形上的模擬,不會有內在的美存在,這樣的古拙用筆的魅力會大打折扣的。陳老蓮早年學習歐陽通的道因碑,中年繼學懷素,兼學褚遂良、米芾之長,并得力于顏真卿的《三表》,遂自出機杼形成了結體奇特別致、運筆剛柔互濟、遒勁灑脫、富有節奏感、逸趣橫生、超然卓立的書風。所以陳老蓮的書法根基是很深厚的。因此他在繪畫中書法用筆保障了勾線的骨力和書法韻味之美。無疑這也對突出古拙畫風的品質形成了堅強的后盾。
幾乎可以這么說,古拙與猥瑣只是一墻之隔,在同樣造型情況下,有堅挺書法底蘊的支持就可形成古拙美,沒有堅挺書法底蘊的支持就是猥瑣丑。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繪畫的品質保證在于筆墨和造型,比如筆墨功力差些但造型好,那么還有美的造型在。而將二者都屏棄,那么,用貧弱的線條描繪丑陋的形象,猥瑣成為必然還有什么疑義嗎?
我們明白了古拙與造型和筆墨的關系就會明白繪畫注重形象的重要性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曾興起一股新文人畫風,內中不乏一些故意描繪成蹩腳形象的仕女圖。這些在外形對仕女進行夸張也好,標新立異也好,除性的描寫是讓老蓮臉紅道不及的,其它藝術的建樹離陳老蓮的水平尚甚遠。尤其在筆墨上完全失去了傳統,此種“學畫舍中國原有最高之學識,而務求貌似他人之幼稚行為”,確實“是無真知”的表現。(黃賓虹語)而在此風的影響下,蹩腳的猥瑣人物形象似乎也曾波及畫壇漸成潮流。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