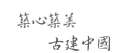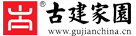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位于浙江中部的富春江,長約110公里,流貫浙江省桐廬、富陽兩行政區(qū)。泱泱江水,宛若明鏡,兩岸青山點(diǎn)點(diǎn),似如粉黛。元代黃公望的一尺《富春山居圖》,更是畫出了富春江兩岸的詩意生活。
如今,富春江兩岸許多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村落集鎮(zhèn),吸引了各地設(shè)計(jì)師、藝術(shù)家和商人來此改造老宅,或在此常住,在這些偏僻村落發(fā)起烏托邦似的理想。外來者的舉動(dòng)可以視為對當(dāng)下急遽推進(jìn)的城市化進(jìn)程的一種反思,也是一股時(shí)代的“逆流”。
普利茲克建筑獎(jiǎng)獲獎(jiǎng)?wù)咄蹁?年時(shí)間,率先在富陽文村打造出了14幢民居。他的經(jīng)驗(yàn)和觀點(diǎn),或許可以啟發(fā)我們對鄉(xiāng)村規(guī)劃設(shè)計(jì)的新思考。

從2012年開始,王澍和同是建筑師的妻子陸文宇一趟趟地奔向這個(gè)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村莊,用灰、黃、白的三色基調(diào),以夯土墻、抹泥墻、杭灰石墻、斬假石的外立面設(shè)計(jì),呈現(xiàn)他理想中的美麗宜居鄉(xiāng)村。
建筑師王澍說,自己正在挑戰(zhàn)建筑界最難的領(lǐng)域:農(nóng)居房。當(dāng)然,“最難”兩個(gè)字是王澍自己加的。在全國范圍內(nèi),每一天都出產(chǎn)著各種類型的農(nóng)居設(shè)計(jì)圖,每一天都涌現(xiàn)出各種風(fēng)格的鄉(xiāng)村民居,但他在富陽洞橋鎮(zhèn)文村設(shè)計(jì)建造的14幢24戶農(nóng)居,從規(guī)劃到落地,整整花了3年。
十多年對浙江鄉(xiāng)村的觀察和理解,讓王澍這位出生于新疆的西北漢子有驚喜有遺憾:“浙江的古村落里,有一大批代表很高建筑水平的江南民居,但城市的建造風(fēng)氣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進(jìn)入了鄉(xiāng)村,大家向往高樓洋房,這些民居也難逃被拆的命運(yùn)。”王澍說,“老房子就是活著的歷史,歷史都沒了,還有什么根基?”
王澍記得在2012年,他在富陽的村子里轉(zhuǎn)悠時(shí),遇到了洞橋鎮(zhèn)大溪村的村支書王榮華。那時(shí),王榮華正指揮著一輛鏟車,拆除村里的一幢老屋。王澍激動(dòng)地跑過去,大聲喊停,陸文宇則一路跟著小跑,攔下了王榮華手中正在揮動(dòng)的小旗子。“要是不拆掉,老房子留著做什么用?”王榮華的一句反問倒是激發(fā)了王澍的信心,他拍了拍王榮華的肩膀:“你等等,我來想辦法!”
那時(shí),富陽正力邀王澍為當(dāng)?shù)氐牟┪镳^、美術(shù)館、檔案館“三館”項(xiàng)目做規(guī)劃,從不輕易對外接項(xiàng)目的王澍一口答應(yīng)下來,但他的條件是要在洞橋鎮(zhèn)文村、大溪村一帶,做鄉(xiāng)村民居的整體規(guī)劃。
“農(nóng)居設(shè)計(jì),也許是個(gè)無解的問題,而且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看到很好的樣本。“王澍說,“但是不試試怎么知道不行呢。只有最強(qiáng)的設(shè)計(jì)力量對鄉(xiāng)村感興趣了,只有最強(qiáng)的建筑師團(tuán)隊(duì)進(jìn)駐鄉(xiāng)村了,才可能做出好的解決方案。在這一點(diǎn)上,我義不容辭。”

文村這片古民居,非常漂亮,你是怎么發(fā)現(xiàn)的?
王澍:這是我自己的一個(gè)課題。現(xiàn)在城市的大拆大建,使得城市里的建筑文化傳承幾乎沒有希望了,僅剩的一點(diǎn)“種子”就在鄉(xiāng)村,我希望它還能發(fā)芽。
從2010年開始,我們對全省的傳統(tǒng)村落做了一個(gè)為期4年的調(diào)研,可以說跑遍了浙江,情況很嚴(yán)峻。光是在富陽,200多個(gè)村子,如果以半舊半新、文脈可續(xù)為標(biāo)準(zhǔn),其中僅剩20多個(gè)村還有點(diǎn)希望。當(dāng)然這個(gè)數(shù)據(jù)不是絕對的,或許還有意外的驚喜隱藏在哪個(gè)山溝溝里。文村就是我們調(diào)研中的一個(gè)驚喜。
我的想法是在不改變古村落面貌的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隱形城市化。改造一個(gè)村落稱不上“化”,一定要三四個(gè),并能連成一片,坐兩站村際公交車,轉(zhuǎn)一個(gè)山灣就能到另一個(gè)村莊了,這隱含著一種密度和自然同時(shí)并存的新型城市結(jié)構(gòu),特別適合浙江的情況,而洞橋鎮(zhèn)的大溪村、文村這一片古村落,正是我們要找的“種子”。

在文村古民居改造過程中,你們遇到了哪些難題?在建筑與環(huán)境之間,又怎樣權(quán)衡?
王澍:農(nóng)居問題是很難解決的,甚至一個(gè)屋檐、一堵墻,都可能招來村民的抵觸,這就要求我們設(shè)計(jì)師放低身段,不斷修改設(shè)計(jì)方案。此外,在技術(shù)上,夯土、抹泥等一些老的建筑技術(shù)要不斷創(chuàng)新,尋找新材料、探索新方法,說服村民接受它。為了延續(xù)傳統(tǒng)村落的多樣性面貌,我設(shè)計(jì)了8種不同的房子,同樣的土地上布局了24戶,錯(cuò)落有致,和諧自然,設(shè)計(jì)中考慮到了小院、堂屋、農(nóng)具室、灶屋等,村民們也能接受了。
我的基本觀點(diǎn)是,建筑與環(huán)境的和諧,我們既需要民族的審美,也需要時(shí)代的創(chuàng)新和表達(dá),二者是不沖突的。富陽在美麗宜居村莊建設(shè)推進(jìn)中,能把這么多連片的古民居完好地保存下來,又混合以有文脈傳承的新創(chuàng)造,將為浙江地域建筑文化特征的重塑帶來不可估量的研究示范價(jià)值,也為保持地域鄉(xiāng)愁的新型城市化探索了新路。
我打算花8到10年的時(shí)間,根據(jù)浙江各地不同的建筑風(fēng)格打造七八個(gè)風(fēng)格迥異的美麗宜居村莊樣本。就像文村這種樣本,既有“浙江味道”,也有中國建筑的特點(diǎn),還有推廣價(jià)值,能傳下去。

作為“總設(shè)計(jì)師”,你對文村這片古民居的改造有怎樣的構(gòu)想?
王澍:浙江的鄉(xiāng)村建筑原本達(dá)到了一個(gè)很高的審美水平,絕不遜于瑞士鄉(xiāng)村建筑,但都沒有了,而新建筑又缺乏文化脈絡(luò),甚至可以說一個(gè)比一個(gè)丑。
我們以保護(hù)老房子為前提,對那些老村中如癌癥細(xì)胞的新民居,解決方案有兩種:一是就地重建,遵循整舊如舊原則,目前已試點(diǎn)7戶;二是深度改造,不是簡單的外立面刷刷,而是像老中醫(yī)把脈一樣,望聞問切,根據(jù)每個(gè)房子不同的風(fēng)格進(jìn)行深度改造,比如,是夯土建筑的,就用新夯土技術(shù)改造;是磚結(jié)構(gòu)的,就去掉那些難看的瓷磚,用我們美院研究的抹泥技術(shù)來改造;是杭灰石壘砌的,我們找來村里的20多個(gè)石匠,讓他們也參與進(jìn)來……
“我很想知道文村會(huì)怎么發(fā)展。比如農(nóng)民住進(jìn)新房后,他們是否習(xí)慣?社會(huì)性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力量的加入,如何引導(dǎo)鄉(xiāng)村的經(jīng)濟(jì)業(yè)態(tài)轉(zhuǎn)型?還有各種對鄉(xiāng)村感興趣的人,會(huì)給文村帶來怎樣的變化?”王澍說,“我們就像在湖面上投下了一顆石子,也想讓更多的人參與討論、關(guān)注鄉(xiāng)村,這樣,鄉(xiāng)村的復(fù)興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