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對于茶禮,對于文雅風尚到底追求到什么程度?
除了宋徽宗著下《大觀茶論》,在宋代科舉中或許也能窺見一二。
宋代科舉實行“鎖院”制度,考生們禁錮于貢院50余日,既是改變命運的50日,也是50日的高壓牢籠。
鎖院中的“茶禮”,不僅是禮儀,也是維系考生生理與精神平衡的核心媒介。考生們每日“晨昏二茶”,晨茶提神,喚醒昏沉神志,昏茶安神,緩解應試焦慮。

茶湯由官窯青瓷盛裝,象征“器以載道”;茶渣需集中掩埋于貢院“凈地”,違者以“褻瀆斯文”論罪。
那茶湯的滋味,分明浸透了士子的忐忑與希冀。
晨昏二茶時,需舉行奉茶儀式。考生躬身接盞,雙臂需低于耳垂,盞不得過肩。此為以體正心”的儒家訓誡。
茶具的形制亦隱含秩序:青瓷茶盞素樸無紋,呼應“清廉儉德”的士人價值觀;而茶湯分配由巡茶吏嚴格監控,七分滿為常態,滿盞則暗含考場異動警示。
巡茶使是宋朝特有制度,與“巡查使”相近。該職位多為退休的翰林兼任,負責防止作弊與教化學生。
他們是暗處的獵鷹:翻檢茶盞內壁是否暗藏夾帶,審視茶托夾層可有玄機;觀察分茶深淺,七分滿意為“平安無事”,滿盞則成“事有蹊蹺”的暗號。
也是儀態的判官:接盞需雙手高舉過肩,肩線不得越耳;飲時不得有聲,茶碗不離案幾。若誰手顫如篩糠或飲如牛汲水,卷宗上立時便添一筆“心浮氣躁”——科舉場上的品行考評,便在杯盞起落間定下乾坤。

宋代的醫書上,也有著對茶禮道德的規勸。
煙霧繚繞的宋代貢院,空氣中彌漫的不僅是茶香,更有一股無形的、令人屏息的壓力。
醫官們熟讀《太平圣惠方》,皆知茶性本寒,能“醒昏聵,滌濁揚清”,是提神醒腦、舒緩焦慮的良方。
然而,當這尋常藥草汁液注入貢院的青瓷官盞,其本真的藥理便被一雙無形的手悄然篡改。
朝廷的諭令與考官的宣講,日復一日地在狹窄的號舍間回響。晨起那碗濃得發苦的提神茶,不再僅僅是驅趕睡意的湯藥。監考官肅立在旁,目光如炬,宣稱此乃“皇恩浩蕩,特賜醒志之湯”,意在“喚醒爾等濟世安民之宏愿”。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尋常茶渣,在貢院中也仿佛成為了神圣的代言。
每每喝完茶,考生們需小心翼翼,將其恭敬地捧至貢院深處指定的“凈地”,如埋藏珍寶般深深掩埋。
若有疏忽,隨意丟棄,便是觸犯“褻瀆斯文”之大忌,輕則招致申斥,重則前程盡毀。角落里供奉著的粗陶茶碗,亦不再是簡陋器皿,而被賦予了“清廉儉德”的象征意義,無聲地提醒著士子們應恪守的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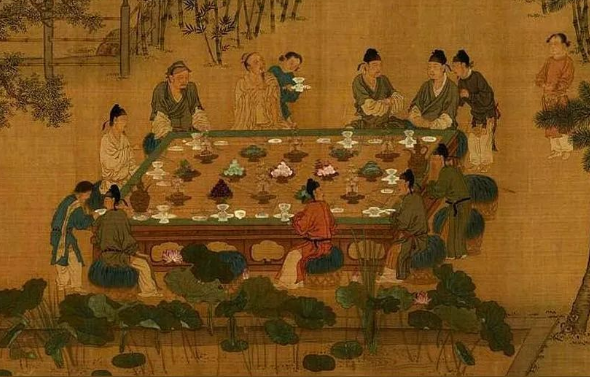
于是,在這彌漫著茶香的封閉牢籠里,文人的精神世界被悄然重塑。每一次躬身接茶,每一次無聲啜飲,每一次對茶渣的頂禮膜拜,都像一把無形的刻刀,日復一日地雕琢著他們的身姿與心性。
苦茶的滋味,不再僅僅是舌尖的感受,更成了“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這一圣賢箴言的強制注腳。藥香彌漫處,無形的道德枷鎖已然鑄成,緊緊縛住了貢院中每一個渴望躍龍門的身影。
宋朝的茶,既有著風雅,也有著懦儒;有著雅志,也有著滑稽。
一盞貢茶,半部科舉沉浮錄。
當茶寄托著文化,呈現的是從物質需要上升到精神文明的一種斑斕的美好。但對于任何一種文化來說,過度詮釋都是大忌。
晨昏二茶,如果用作放松神志,便是雅事,可帶上了規矩的枷鎖,那便成了滑稽的做作了。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