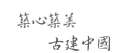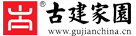徽州古民居,既是中原文化與山越文化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又是儒釋道多家文化的結(jié)晶,傳統(tǒng)文化意味十足,但其中蘊(yùn)藏著新變的理念。這主要體現(xiàn)為:樓居方式是干欄式建筑與中原建筑文化的融合;在型制上是因地制宜和而不同的展現(xiàn);在風(fēng)水上改風(fēng)改水為徽人服務(wù);在色彩上蹊徑獨(dú)辟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天井的設(shè)置是北方四合院在徽州的轉(zhuǎn)型;小部件斗拱有著獨(dú)特的象征意味。
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曾說過,人的思想就像宗教一樣也有其紀(jì)念碑,這就是建筑。徽州古民居,是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杰出代表。1999年12月,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入選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huì)這樣評(píng)價(jià):“西遞、宏村這兩個(gè)傳統(tǒng)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那些在上個(gè)世紀(jì)已經(jīng)消失或改變了的鄉(xiāng)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風(fēng)格,古建筑和裝飾物,以及供水系統(tǒng)完備的民居都是非常獨(dú)特的文化遺存。”
徽州在歷史上是個(gè)移民社會(huì),中原的精英人士南遷后,汲取了中原和土著的文化精華,彰顯出巨大的包容性和創(chuàng)造性。徽州古民居體現(xiàn)了儒家、道家、釋家等多種文化的交融,“涵義最完美的建筑歷史,幾乎囊括了人類所關(guān)注的全部事物。”徽州古民居是在農(nóng)業(yè)文明的基礎(chǔ)上,加上徽商文化的傳統(tǒng)凝聚而成的,其間滲透著新變理念,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六個(gè)方面。

樓居:干欄式建筑與中原建筑文化的融合
徽州的土著居民為山越人,在長期的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生存經(jīng)驗(yàn)。他們在山間潮濕、多雨的亞熱帶氣候環(huán)境中,采取干欄式建筑模式——樓居結(jié)構(gòu)。山越文化“是開發(fā)江南山區(qū)的先民在一個(gè)相當(dāng)長時(shí)間里,吸納融會(huì)多種文化而逐漸生成的新質(zhì)文化,其中包括原住民文化,吳、越和楚文化成分,甚至包含良渚文化若干因素”。良渚文化的房屋以木構(gòu)為主。干欄式木樓為穿斗式木結(jié)構(gòu),木材從當(dāng)?shù)氐纳街芯偷厝〔模话銥樯寄荆课莸拈_間不大。西晉的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變,中原地區(qū)戰(zhàn)事頻發(fā),民不聊生,北民大舉南遷,徽州山高多屏障,如世外桃源一般,成了北民避難的勝地。南遷的居民,帶來了先進(jìn)的中原農(nóng)業(yè)技術(shù),也帶來了先進(jìn)的建筑文明。當(dāng)先進(jìn)文明融入到后進(jìn)文明后,發(fā)達(dá)的中原文化很快就反客為主了。北方的合院采取抬梁式架構(gòu),用材粗大,開間也比較大。徽州民居樓居式的結(jié)構(gòu),大多采用兩層樓,也有少數(shù)三層樓,有的在地面上鋪設(shè)木地板,用來通風(fēng)隔潮濕,避免濕氣直接對(duì)人產(chǎn)生影響。徽州民居“汲取了干欄樓居開敞的堂屋和挑臺(tái)特征,將正中廳堂擴(kuò)大并半敞開,與天井空間連成一片”。在廳堂部分采取抬梁式結(jié)構(gòu),空間的跨度較大;在空間較小的臥室則采用穿斗式結(jié)構(gòu)。
中原地區(qū)農(nóng)業(yè)文明發(fā)達(dá),長期為政治文化中心。其建筑文化以北方官式建筑為基礎(chǔ),強(qiáng)調(diào)儒家的倫理道德秩序。到了徽州后,徽民重視宗祠建設(shè),維護(hù)同一氏族的權(quán)威,在建筑中體現(xiàn)等級(jí)化,甚至直接用門聯(lián)、匾額體現(xiàn)封建的倫理秩序,廣設(shè)牌坊標(biāo)志。諸多的建筑形式,都能體現(xiàn)出中原建筑文化重倫理的痕跡。在傳統(tǒng)的男耕女織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里,女性在家庭中是沒有地位的,男性是家中的家長,是家中的絕對(duì)權(quán)威。就民居空間的使用來說也是如此,嚴(yán)格的女教觀念使婦女的活動(dòng)區(qū)域很小,大戶人家的女孩在出嫁前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在閣樓里終日學(xué)習(xí)女紅或者撫琴作畫。閑暇的時(shí)候,也只能待在美人靠邊欣賞室內(nèi)的風(fēng)景。

型制:因地制宜、和而不同的展現(xiàn)
徽州山多地少,人口多,可耕地較少。在為數(shù)不多的平地上建造房屋,宅基地顯得比較局促,民居的建筑布局緊湊。加上明朝時(shí)期,皇家對(duì)建筑的規(guī)定很多,住房的等級(jí)也會(huì)根據(jù)官員的級(jí)別不同有所差異。明朝對(duì)建筑規(guī)定森嚴(yán),據(jù)《明史·輿服志》記載:藩王稱府,官員稱宅,庶人稱家,住宅建造大小亦受限制。王侯、官員按等級(jí)造房,庶人只能造“三間五架”之屋。
徽州民諺有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刺激了徽州重商的傳統(tǒng)。徽商在明清之際,馳騁中國商場幾百年,甚至有“無徽不成鎮(zhèn)”之說,可見徽商的足跡遍布中國;徽商的繁榮極盛,富可敵國,可見當(dāng)時(shí)徽商的影響力。發(fā)跡后的徽商回到家鄉(xiāng)買田置地,榮歸故里,大興土木,建造了很多的民居建筑和祠堂、牌坊、書院等公共建筑。雖說地處山高皇帝遠(yuǎn)的徽州,但皇家對(duì)建筑的規(guī)定徽商是不可違背的,只有另辟蹊徑,在新變上做足文章。
在山光水色的映襯下,徽州古村落宛如“中國畫里的鄉(xiāng)村”,魅力四射,韻味無窮。從外觀上來看,青磚、黛瓦、馬頭墻,這是徽州民居的共性之處,但具體到每一家每一戶,又會(huì)根據(jù)宅基地的大小、地形、地勢,結(jié)合主人的個(gè)性和審美追求,呈現(xiàn)出不同的風(fēng)貌。穿行于徽州民居間的小巷,置身其間,經(jīng)過每家每戶,從門樓到房屋的裝飾,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兩戶,這就是徽州民居的獨(dú)特之處,也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和而不同”。
風(fēng)水:改風(fēng)改水為徽人服務(wù)
徽州民居追求“枕山、環(huán)水、面屏”,形成枕山環(huán)水、依山傍水、背山面水的格局。在徽人眼中,理想的村址是符合風(fēng)水觀念的,要遵循“陽宅須教擇地形,背山面水稱人心,山有來龍昂秀發(fā),水須圍抱作環(huán)形,明堂寬大斯為福,水口收藏積萬金,關(guān)煞二方無障礙,光明正大旺門庭”。徽人重視風(fēng)水由來已久,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說:“風(fēng)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平時(shí)構(gòu)爭結(jié)訟,強(qiáng)半為此。”王明居先生認(rèn)為:“風(fēng)水,就其存在狀態(tài)而言,是客觀的。它是大自然的產(chǎn)物,因而有它的自然性。具體地說,它是特定時(shí)間、空間中的自然山水風(fēng)貌,是建筑所處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風(fēng)水本身是獨(dú)立于人的意識(shí)之外的客觀存在,它是沒有意志的。但是,風(fēng)水觀念卻是人對(duì)風(fēng)水的認(rèn)識(shí),因而是主觀的。我們絕不可把風(fēng)水與風(fēng)水觀念混為一談,把客觀與主觀混為一談。”
徽人在建造房屋的時(shí)候,遇到風(fēng)水不符的,就得改風(fēng)改水。比如徽州的風(fēng)水鎮(zhèn)符石敢當(dāng)。石敢當(dāng)為長方形石碑,通常被置于村落入口處、河流池塘岸邊、門前巷口、三叉路口直沖處等,有的鑲嵌在墻中,有的獨(dú)立放置。歙縣漁梁某宅因門正對(duì)紫陽山上一怪石,故將門偏斜朝向紫陽峰,同時(shí)在門前立“泰山石敢當(dāng)”。黟縣城內(nèi)很多民宅將門遠(yuǎn)離沖巷處,而在直沖巷子的墻角處立一塊“泰山石敢當(dāng)”。
徽州很多村落四面皆山,形成相對(duì)封閉的空間。水口是進(jìn)入村落的咽喉,在村民眼中水口關(guān)系到村落人丁財(cái)富的興衰聚散。為了留住財(cái)氣,除選中好的水口位置外,還必須建筑橋臺(tái)樓塔等物,增加鎖鑰的氣勢,扼住關(guān)口;同時(shí)也改善了村落的環(huán)境及景觀,形成“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村落總體環(huán)境特征,使水口成為徽州的村落庭園。除了水口林,還有根據(jù)風(fēng)水“障空補(bǔ)缺”理論的需要,建造文昌閣、奎星樓、廟宇等建筑,改變徽州的風(fēng)水為徽人服務(wù)。

色彩:蹊徑獨(dú)辟中的至高追求
明清時(shí)期的建筑裝飾用色,有著深刻的等級(jí)觀念,王公、大臣與庶民在建筑上的差異很大。北京故宮等宮廷建筑光彩照人、金碧輝煌,大多采用黃色、紅色、金色進(jìn)行裝飾,紅色代表神權(quán),黃色昭示君權(quán),充分體現(xiàn)出神權(quán)和皇權(quán)的至高無上,呈現(xiàn)出一種“錯(cuò)彩鏤金”之美。
徽州古民居,是徽商出資建造的。受等級(jí)森嚴(yán)的建筑制度的影響,建筑裝飾只能避開“錯(cuò)彩鏤金”之美。徽商的活動(dòng)區(qū)域很廣,并且多在外鄉(xiāng)經(jīng)營,在家鄉(xiāng)采用低調(diào)的色彩可以確保家鄉(xiāng)的財(cái)產(chǎn)安全。加上程朱理學(xué)對(duì)徽州影響深遠(yuǎn),朱熹主張平淡自然,在色彩上傾向于中和的無彩色,生活在山水之間的徽民逐漸造就了徽州民居清新、淡雅、潔凈的建筑風(fēng)貌。在色彩的選擇上,人們喜愛色度偏低、色調(diào)中性的調(diào)和色,用黑、白、灰作為主色調(diào),加上與青山綠水協(xié)調(diào)一致,給人以“出水芙蓉”之美。“在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中,白色具有多向性,表示光明之源,在徽州許多建筑中高聳延伸的白墻幾乎與淺色天空連成一片,追求真正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黑色則象征天,它源于夜幕之神秘;而青灰色則與五行中的水相對(duì)應(yīng),寓意著避免水災(zāi)。”
天井:北方四合院在徽州的轉(zhuǎn)型
中原土地平坦遼闊,宅基用地相對(duì)充裕,民居采用寬敞的四合院院落式建筑,隨著中原士族的南遷,到了土地緊缺的徽州,沒有足夠的土地建院落,闊大的四合院變成了建筑物內(nèi)部的天井。這一轉(zhuǎn)型前后,基本的精神還是相通的,就是住宅的自然化,充分體現(xiàn)了古代的天人合一的觀念。所謂住宅的自然化,就是把室外的空間“借”到室內(nèi)來,天井是建筑的一個(gè)有機(jī)組成部分。這是因?yàn)闋I建者受到傳統(tǒng)生命哲學(xué)的深刻影響,認(rèn)為人與自然是血肉相連、同心同構(gòu)的。
徽州的天井,除了有采光、形成小氣候等功能外,還是連接大門與廳堂的中介。廳堂是全家人的中心活動(dòng)區(qū)域,也是會(huì)客的主要空間。坐在廳堂內(nèi),通過天井可以感受到四時(shí)之變,陰晴圓缺,云卷云舒,晨淋朝霞,夜觀星斗,不僅可以安頓性靈,還能愉悅情性。室內(nèi)空間的有限,通過天井走向了無限,個(gè)人心中的小宇宙與天地的大宇宙連成了有機(jī)的整體。正如張世英先生所說:“每一物、每一人、每一部分、每一句話、每一交叉點(diǎn)都是一個(gè)全宇宙,但又各有其個(gè)性,因?yàn)楦髯员憩F(xiàn)了不同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方式,或者說,各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惟一的全宇宙。”[7]在這種相通之中體現(xiàn)生命或者生活的意義與價(jià)值。
徽商長年在外經(jīng)商,財(cái)源來自四面八方,希望圖個(gè)吉利。水主財(cái),故而“四水歸明堂”。天井四周的屋頂坡面,東西南北四面的雨水通過小青瓦流入家中,意味著肥水不外流,象征著財(cái)氣的匯集。這種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也是徽派古民居營建者心理的折射。
天井是虛實(shí)的統(tǒng)一體。天井可以分為井口、井身和井底三部分,井口和井底是可視的,是有形的實(shí)在,井身是不可視的,是無形的虛空,但正是這虛實(shí)的結(jié)合,才成為徽州古民居中獨(dú)特的天井的結(jié)構(gòu)。這種虛實(shí)相生,實(shí)現(xiàn)了生命的超越。雖在廳堂之內(nèi),心系浩渺寬廣的宇宙時(shí)空,使居者不囿于廳堂,而是通過天井實(shí)現(xiàn)與天地宇宙的合二為一。主人在堂前玩味天井,獨(dú)享人生的快樂。宗炳的《畫山水序》認(rèn)為,在“澄懷味象”中,最終“萬趣融其神思”,審美主體在“暢神”中獲得了物我的根本同一。
斗拱:小部件呈現(xiàn)的象征意味
斗拱在中國建筑技術(shù)中是一大創(chuàng)造,是作為承重構(gòu)件而產(chǎn)生的。“它一般總是出現(xiàn)在較大型較重要的建筑物上,久而久之,便成為社會(huì)權(quán)貴、統(tǒng)治者政治倫理地位、等級(jí)與品格的建筑象征。發(fā)展到封建社會(huì)的中后期,便只有宮殿、帝王陵寢、壇廟、寺觀及府邸等一些高級(jí)建筑才允許在立柱與外檐的枋處安設(shè)斗拱,并以斗拱層數(shù)多少,來表示建筑的政治倫理品味。
徽州的如意斗拱呈現(xiàn)出吉祥意味,是中國傳統(tǒng)斗拱之美的積淀與升華,有著徽州工匠的獨(dú)創(chuàng)性。一方面起到負(fù)重的作用,還有著突出建筑磅礴氣勢的審美作用。斗拱部件單純,組合明朗,但結(jié)構(gòu)復(fù)雜,多樣統(tǒng)一。“它以絢爛多姿、五彩繽紛的藻飾涂抹造型,使它那簡潔的構(gòu)架形式又增添了繁縟的色澤與光輝。”
“徽州人在建造斗拱時(shí),還能因地制宜,在寧靜、寂寞、偏僻的山水之間,既顯示出斗拱的隱秘性、深邃性,又突出它的流動(dòng)美、峻拔美。同時(shí),為優(yōu)美的徽州建筑增添壯美,為優(yōu)雅的山區(qū)注入活力,使青山綠水顯得更有生機(jī)。”這與北方不同,北方的平原區(qū)域,沒有青山綠水的映襯,斗拱顯示出的則是雄渾豪放之氣。
梁思成先生曾說:“建筑之始,產(chǎn)生于實(shí)際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著意于創(chuàng)新形式,更無所謂派別。其結(jié)構(gòu)之系統(tǒng),及形式之派別,乃其材料環(huán)境所形成。”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不能全部脫離以往的傳統(tǒng)基礎(chǔ),總是在基礎(chǔ)之上進(jìn)行創(chuàng)新,在徽州古民居中,多種文化的交融與滲透,形成了獨(dú)特的古民居樣式。創(chuàng)新,是民族的靈魂。這些新變的理念進(jìn)而轉(zhuǎn)化為徽州古民居的現(xiàn)實(shí)構(gòu)造,是徽州匠人的創(chuàng)造,也是徽商的創(chuàng)造,更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自身內(nèi)部的創(chuàng)新,值得我們深思和總結(jié)。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