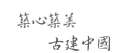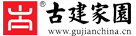2019年,立足田野、有效保護,是石峁考古歷程中平凡卻不平淡的一年。之所以平凡,是因為本年度工作接續上一年,工作地點不曾變換,考古隊員們依舊在皇城臺上揮灑汗水;之所以不平淡,是因為突然涌出的顛覆性發現不斷挑戰我們已有的認知,而這些新發現再次將石峁遺址推上“十大”和“六大”的榮譽殿堂。
1、大臺基規模遠超預判
2018年深秋,在完成皇城臺門址和東護墻北段上部的發掘后,我們沿門址主門道內的路面繼續向上進行摸索式發掘。在皇城臺臺頂發現了一座夯土筑芯、砌石包邊的“石包土”式大型建筑臺基,即現在所稱的“大臺基”。時至歲末,僅將大臺基南護墻自東向西清理至80米處,墻體似有拐折跡象,故首次認知的大臺基規模“東西長度超過80米、殘高約4米”。是年,已有30余件石雕破土而來。

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11號石雕細部
2019年的接續發掘打破我們最初的認識。大臺基的南護墻并未止于80米處,石墻還在繼續向西延伸。我們的探溝也順著石墻的走向繼續向西布設,終于確認了大臺基的西南角,經測量東西長度竟然超過130米。在確認了大臺基的東西范圍后,我們開始在四周進行摸索發掘,進一步尋找并揭露大臺基的輪廓范圍。

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東段鳥瞰
又一個深秋,終于探明了大臺基西側、北側護墻的位置及走向,經測量,大臺基平面基本呈圓角方形,四邊長度大致相當,約130米,總面積達16000余平方米。就目前國內同時期的考古發現來看,如此大體量的高臺式建筑基址實屬罕見,單就起建規模而言,已初具秦漢帝國及后世宮室“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的恢宏氣勢,大臺基的修建,想必正是這種“非壯麗無以重威”的思想穿越古今的共鳴。
2019年對大臺基南護墻進行了基本完整的揭露(西端因現代墳園暫緩發掘,但不影響大臺基和南護墻結構和規模的判斷),西段50米的墻體上又發現了30余件石雕,連同2018年的發現,石雕總數已達70件。
這些石雕多數出土于南護墻墻體的倒塌石塊內,有一些依然鑲砌于南護墻墻面上,除平面浮雕式樣的人物、動物、“神獸”、符號等幾類石雕外,新發現的一件立柱式石雕尤為引人注目。在大臺基南護墻南側存在有一道石砌矮墻,走向與南護墻基本平行,依據其性質和用途,稱作“夾墻”。夾墻與南護墻之間形成寬約9米的夾道,地面以黃沙土鋪設,平整硬實。

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47號石雕位置及出土狀況

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47號石雕(仰視)
這件編號為47的立柱式石雕恰矗立于夾道中部的地面上之外,與夾墻和南護墻的距離基本相當。石雕為扁圓柱體,直徑約50厘米,高于地面約1米。圖像在圓柱頂部和柱身兩寬面上,浮雕而成。柱頂平整,邊緣略有殘缺,周緣雕出寬約2~3厘米的條帶。中央有一圜底小圓窩,圓窩周緣對稱雕出呈十字分布的四組“Y”形紋樣,將平面四等分,“Y”形紋樣間又雕有同心圓。整體觀察,似可解讀為以“Y”形紋樣為鼻、同心圓為雙眼、中央小圓窩為嘴呈旋轉式連續分布的4副面部形象。柱身兩面均浮雕出神面,兩側圖案基本一致。神面頭上戴冠,冠兩側有上下翻卷的發式;鼻呈“王”字形,鼻梁纖細,鼻翼寬大,上有“Y”形裝飾;“臣”字形雙眼,向上外斜;闊嘴,咧口露出牙齒;下巴處有似胡須的“火”字形紋樣;雙耳雕于柱身窄面,呈垂滴狀,佩飾耳珰;整體顯得面目猙獰,但一些細部卻又十分生動傳神。與之前發現的平面式嵌入石墻的石雕不同,立于地表的47號立柱式石雕更具標志性的功能,功能與用途類似于圖騰柱,但在雕刻的內容及風格方面,這件立柱式石雕與平面式石雕基本一致,一起承載著石峁先民們的精神信仰。

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11號石雕拓本
對于這些珍貴石雕的細節展示和記錄,在“絞盡腦汁”之后,我們采用了電子拓片的處理方式,取得了多重滿意的效果。畢竟,傳統印拓會傷及文物本身,而線圖勾勒則無法達到圖像本身傳神生動的表現目的。
2、首次發現蛇紋鬲時期的石砌院落
為了解大臺基頂部的建筑布局,2019年還對臺頂進行了小面積揭露。在臺基西南部,發現了一處下挖修建的由3座石砌聯排房址構成的院落遺存,稱為“一號院落”。院落平面呈南北向長方形,規模宏大,南北長22米,東西殘寬15米,面積超過300平方米。院墻由規整的砂巖石塊砌成,石塊之間以草拌泥黏合。院落墻體保存狀況不佳,根據院落內房址的門道朝向,推測院門應該在西側。
院落內發現一組連排石砌房址,房址共3座,均坐西面東,彼此間相互倚靠。其中F1為主室,位居中心部位,面積最大,超過50平方米,南、北兩側分別為F2、F3,兩側房址略小,應為側室,面積約30平方米。
在發掘中,一號院落最大的F1的灶面上出土有1件完整的蛇紋鬲,這為我們準確判斷院落的時代提供了依據。根據目前發現的層位關系,“蛇紋鬲遺存”所在的房址和院落年代晚于石峁文化的主體年代。在之前皇城臺的發掘中,曾在上部的地層堆積內(皇城臺主體建筑倒塌堆積之上)發現有此類遺存的殘片,卻始終未能發現這一時期的遺跡。
2019年一號院落的發現,系首次在石峁遺址內揭露出本時期的遺跡,當為皇城臺廢棄后新的族群在此活動的遺孓,為確定皇城臺的廢棄年代提供關鍵性證據。

一號院落(上為東)
這類以蛇紋鬲為典型器類的文化遺存主要分布于河套地區,其中以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朱開溝遺址的發現最為豐富,有學者據此稱之為“朱開溝文化”。但至今學術界對其年代認識還較為含糊,籠統地認為時代在夏商時期,而其文化內涵、分期、源流等問題仍訴訟不休。
這類遺存與石峁文化的分布范圍基本重合,已發現的多處地層證據表明,其年代晚于石峁文化;從文化面貌上看,兩者在陶器上差異是明顯的,但在石構建筑方面卻顯示出一定的承襲關系,兩支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目前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相信隨著石峁遺址進一步的考古發掘,或許還會有“蛇紋鬲遺存”的發現,也許將來會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契機。
3、因地制宜探索保護之路
如何加強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的統籌協調、有效融合是我們在工作中直接面臨并一直不斷思索的問題。作為承擔考古發掘工作的業務人員,對這些自己親手發掘出來的重要遺跡現象不僅應負責挖,更應負責保,因而在工作中主動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配合地方政府,對遺址的后續保護和展示利用工作積極建言獻策,是我們的職責與擔當。

氣肋膜保護大棚
石峁遺址所在陜北地區夏季降雨集中,極易形成暴雨,加之遺址土質結構較為疏松、含沙量高,夏季暴雨容易造成的山體滑坡及石墻垮塌,成為文物保護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每逢夏季烏云壓頂之時,其他的考古隊常常可以借天公作美小憩片刻,而我們則如臨大敵,如芒在背。考慮到將來的展示開放及申遺的需要,皇城臺已發掘區域需要裸露展示,過去我們也曾嘗試過在汛期用帆布、塑料薄膜對石墻進行遮蓋,無奈效果不佳,很多文保專家也曾多次赴現場實地考察,但也未形成統一的保護意見。
2018至2019年,我們通過請教當地群眾,咨詢有關專家,同時結合在南美洲瑪雅和印加石構遺址取得的“真經”,在石峁遺址管理處的大力配合下,摸索實踐出一套對石墻進行常態化養護的保護模式。我們經過局部試驗后,將黏土、白灰按照一定比例粉碎、混合,對經雨水沖刷墻體石塊間出現的裂隙填塞補縫,在已發掘的皇城臺門址的墩臺、門道地面及東護墻階梯狀石墻頂部鋪設一層厚約5~8厘米的防水層,既可以防止雨水滲入墻體,又易與遺跡本體剝離鏟除,操作簡單、具有可逆性,效果明顯。
為了保護仍留在大臺基南護墻上的石雕,我們在南護墻中段精心設計并修建了一座氣肋膜保護大棚。采用地面式結構,直接由配重塊固定于地表,電腦控制定時自動充氣,具有不打樁、不開挖、可移動等優點。即使珍貴文物免遭了風吹雨淋,又防止了在保護建筑修建過程中對地下文物的再次破壞,也不影響之后的航拍記錄工作。
皇城臺的發掘工作已經進行了四個年頭。四年來,雖數易寒暑、波瀾不驚,但皇城臺上的考古人依舊熱情不更、初心不改;四年來,皇城臺上的風景看似變化不大、平淡不奇,但早已成為石峁守護人心中的最美景區、無上圣地;四年來,考古工作已經邁出探索“石峁王國”的重要一步,石城專題調查、聚落等級劃分,當然還有府谷寨山的重大發現。雖遭奔波,但我們滿懷欣慰之情迎接著石峁那由遠及近的身影。大臺城、大臺基、大房子、玉器、石雕、銅器、象牙等高等級遺跡遺物無不堅定著我們對皇城臺的認識和判斷。皇城臺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區域,或許應該定其性質為“石峁宮城”。石峁周邊的調查和發掘也在不斷地告訴我們,石峁不孤、石城不孤,周邊石城以眾星拱月之勢維系著石峁城的核心地位,都邑、王國,逐漸浮出我們認知石峁的海面,石峁都邑身后的石峁王國影影綽綽、相伴而來。

2019年最后出土的石雕
四年來,最喜在巍巍皇臺上舉目四望,看近處斜陽照墟落,望遠方平林漠漠、禿尾寒煙。2019年的最后一天,再一次登上皇城臺。此刻的皇城臺銀裝素裹、惟余莽莽,遠處是頓失滔滔的禿尾河,天地之間只剩空靈,頗似“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之景,讓人不禁升起“窗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之情,此景此情一定是石峁的犒勞、皇城臺的饋贈,讓我們享受這平靜的美好,準備迎接石峁下一年的精彩。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