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明清時期,祭祖是相當(dāng)普遍的禮制實踐,許多世家大族設(shè)有祠堂。然而對于不設(shè)祠堂的宗族而言,供奉紙上祠堂就成為了一種常見形式。據(jù)《肥鄉(xiāng)縣志》記載,“士大夫不盡立祠堂,奉神主于寢室,民間多畫祖宗昭穆圖供奉”;另據(jù)《風(fēng)城縣志》,“漢人供宗譜,寬可三四尺……按次開寫先人名氏,男女夭亡者悉列入”。由于紙上祠堂難以保存,現(xiàn)今存世者多制作于清代,早期源流演變已難以詳細(xì)考證。從分布范圍來看,主要集中在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各地尺寸大小不等,規(guī)格較大者高可達(dá)兩米有余。紙上祠堂的造型設(shè)計,從以下典型案例中可以窺見一斑。
豫北滑縣的祖宗軸(圖①)由下至上依次繪有祠堂山門、庭院以及拜殿。祠堂呈白墻灰瓦,山門上涂黑漆,為三間式。正門下設(shè)臺基,配有相向而望的石獅一對,其屋脊上雕脊獸,屋檐下掛蝙蝠,寓意吉祥。門洞上方為庭院,其中繪有數(shù)量可觀的牌位,上書祖先名諱。牌位區(qū)分左右排列整齊,向內(nèi)側(cè)傾斜呈鏡像對稱。庭院靠近偏門處畫有松樹兩棵,另有鹿鶴各一對,牌位、松樹、鹿和鶴皆沿祠堂中軸線呈對稱分布。最靠內(nèi)部的拜殿建筑物為重檐懸山式,正面可見四根黑漆立柱,屋脊上雕有繁復(fù)的脊獸,檐枋飾有彩繪,裝飾華麗。
另一種典型的紙上祠堂形式是山東濰坊的家堂(圖②)。畫面主要部分仍然為白墻灰瓦的祠堂,祠堂山門上懸“先祠”匾額,其后為稱作“追遠(yuǎn)堂”的中廳,內(nèi)設(shè)牌位、香案。中廳旁開兩扇小門,由此得以進(jìn)入二進(jìn)天井,至于拜殿前。拜殿內(nèi)有男女祖先二人,正面朝向觀者,兩位祖先中間的牌位上寫著“始祖之位”,其后的山水屏風(fēng)依稀可見。圖中宗族后世子孫姿態(tài)各異,有騎于馬上者,也有拱手作揖者,多三兩成群彼此呼應(yīng),朝向祠堂門聚攏。后世子孫環(huán)繞祠堂門的排列,以及所有人恭敬的姿態(tài)皆有助于凸顯圖中祠堂建筑物的莊重感。
由以上描述可見,紙上祠堂建構(gòu)了一個始于祠堂山門外,終結(jié)于拜殿,充斥著豐富細(xì)節(jié)的虛擬空間。作為先人象征的牌位與祖先影像都被納入祠堂建筑的空間結(jié)構(gòu)中,按照現(xiàn)實祭祖儀式時的布局得到呈現(xiàn)。那么,紙上祠堂又是如何發(fā)揮禮儀功能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首先回溯至西周的宗廟。《禮記·王制》記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從中可見,宗廟建筑形式與宗法制度結(jié)合在一起,其特點是對世系的強調(diào)。宗廟遵循嚴(yán)格的排列順序,始祖居中,始祖以下第一世居左,稱“昭”;第二世居右,稱“穆”。以下凡三世、五世、七世等奇數(shù)后代皆為“昭”,四世、六世、八世等偶數(shù)后代皆為“穆”。昭穆次序,百世不亂。區(qū)分昭穆的傳統(tǒng)在后世得到了長期延續(xù)。至于宋代,在宗族復(fù)興的理想下,周代的宗法再度被啟用,宋儒試圖借用經(jīng)典中的宗法原則與祭祀禮儀設(shè)計祠堂祭禮,以重建和維持宗族。
作為一個物質(zhì)性的實體,祠堂所提供的建筑空間本身就具有設(shè)定禮儀程序的作用——從祠堂門進(jìn)入、沿中軸線穿過庭院、最終達(dá)于內(nèi)殿前。始祖通常被祭祀于祠堂深處的內(nèi)殿,而近祖則被祭祀于外部的享堂,愈靠近外圍輩分愈低,因此祭拜者從祠堂門向內(nèi)殿行進(jìn)的過程,正是回歸氏族初始的過程。祖先在祠堂中的位置,正如學(xué)者巫鴻多次指出的,隱含著從現(xiàn)時向遙遠(yuǎn)過去進(jìn)行回溯的編年順序,這個順序幫助確定禮儀程序,而這個禮儀程序又使人們重溫歷史記憶,賦予自己的歷史一個確定的結(jié)構(gòu)。《禮記》中不下十次地強調(diào)宗廟禮儀是引導(dǎo)人們“不忘其初”,“返其所自身”,因此在儀式過程中祭拜者的行進(jìn)路線不可打破,否則將無法達(dá)到儀式的效果。
再由建筑轉(zhuǎn)至平面,我們似乎可以認(rèn)為,紙上祠堂的全正面構(gòu)圖中隱含著一種為觀者設(shè)定的觀看模式。當(dāng)觀者的目光沿著既定路線行進(jìn)時,將會依次看見現(xiàn)實祠堂祭祖時所應(yīng)當(dāng)在眼前出現(xiàn)的景象,相反,不應(yīng)當(dāng)被看見的部分則被略去。通過目光移動,觀者得以實現(xiàn)對祠堂祭拜過程的模擬,以此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以山東濰坊的家堂為例,首先,觀者與祠堂門外的后世子孫共享同一條視平線,目光望向祠堂門。而由門洞中進(jìn)入后,則會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一座庭院中,接著繼續(xù)前行,穿過進(jìn)入內(nèi)殿的小門,便能夠到達(dá)以畫像作為象征的始祖跟前。至此,觀者“報本反始”的目光之旅就結(jié)束了,圖中并沒有畫出祠堂“寢”的部分、后部庭院或外圍圍墻,這些空間在現(xiàn)實祭祖儀式中不應(yīng)當(dāng)踏入,也無需被看見,因此便隱匿了。
值得注意的是,圖中逝去祖先的姓名被按照昭穆之世的順序,排列于紙上祠堂中畫出的牌位里,與現(xiàn)實祠堂祭祖時宗族成員的排列方式相仿。其中,二、四、六、八世為昭,居左;三、五、七、九世為穆,居右。宗族女性成員列于其配偶身邊,也在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皆有姓而無名。在靈魂依附于牌位的邏輯下,當(dāng)紙上祠堂于除夕或中元節(jié)被懸掛展開時,祖先能夠通過牌位中自己的名字找到相應(yīng)位置并依附其上,以左昭右穆的方式與參與祭祀的子孫歸屬于同一序列之中。當(dāng)參與祭祀者站立在紙上祠堂前,面對排列有序的祖先時,便得以將自身納入宗族譜系之中,明確自身在其中的位置。
伴隨著需求的增大,部分紙上祠堂以擁有更高復(fù)制性的木刻版畫形式進(jìn)行生產(chǎn)。與手繪祠堂相比,木刻版畫中祠堂時常以變形的方式得到呈現(xiàn)。在濰坊木刻家堂中,祠堂山門、變形后的梁柱與帷帳、拜殿屋檐相互連接形成封閉結(jié)構(gòu),使祠堂輪廓成為包圍先人牌位的邊框。在一些更為廉價的碼子(圖③)中,以祠堂下設(shè)牌位為形象的“家堂”自身成為一尊神,與土地、娘娘、喜神等民間眾神并列,祖先被概念化乃至喪失包括名諱在內(nèi)的所有個性。祭祀完畢后,依俗將碼子焚燒,神便能以紙張為馬,回到天界。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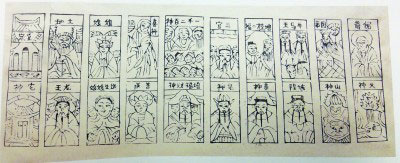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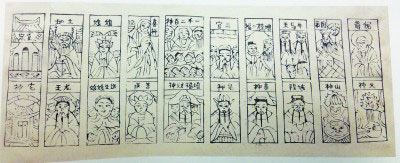
③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