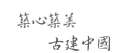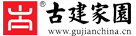在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時期,有一支“黃老學派”,因其尊黃帝和老子為思想源頭,故此得名。其學說在從漢高祖劉邦到文帝、景帝這段時期真正被發(fā)揚光大,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黃老之學才開始淡出官方主流思想。西漢初期,當黃老之術落實在國家政治層面時,給人們的印象通常就是兩個字——“無為”。那么,文景之治的“無為”究竟是何種治國方略?“無為”的施行需要哪些社會條件?
秦制與“黃老之學”并無本質區(qū)別
“黃老之學”中的“老”是指老子,取的是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而“黃”則是指黃帝,也就是指法治——相傳在上古時期,黃帝為華夏各部族立下了統(tǒng)一的規(guī)則,用以仲裁部族間的矛盾,避免華夏族內部因為武力沖突而產生內耗。所謂“黃帝四面”,一種解釋就是黃帝向四方派出人員,以協(xié)調矛盾、治理天下。因此,在戰(zhàn)國時代,黃帝被視為法治的發(fā)端。

“黃老之學”的本意并非是要求國家無所作為,而是指:國家在頒布法律之后,在內政方面就按照既有的規(guī)則來運轉,盡可能避免再做行政干預。
其實自商鞅變法之后,秦的治國邏輯與漢初所推崇的“黃老之學”并無本質區(qū)別。按照秦國的政府機構設置,即使行政機構癱瘓了,只要作為司法機構的廷尉府還在運轉,那么社會依然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正常運轉。
簡單來說,在戰(zhàn)國時代,秦國上層對國家的一切管理,幾乎都是通過“賞”、“罰”兩個動作來實現(xiàn)的。
“賞”指的是“以功得爵”制度。戰(zhàn)國時期,一個人的爵位直接關系到他的社會地位、財富上限以及生活品質。在秦國,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在法律上都有獲得爵位的資格,而得爵的途徑只有一個,那就是立功。秦的受爵制度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打仗、農耕、做工、從政……任何國家想讓你去做的領域,只要你做得足夠好,都可以獲得爵位。而為了保證社會活力能夠持續(xù),秦的爵位是不能世襲的,即便是貴族子弟,也只能通過立功才可以獲得爵位。
“罰”指的是《秦律》中對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的懲治規(guī)定,它們構成了社會生活中的一道道紅線,紅線以內就是人們的自由活動空間。值得一提的,相對于摧殘肉體,《秦律》更多是通過經(jīng)濟懲罰來處置一般性質的違法活動。
一賞一罰之下,秦的國家意圖也就成了老百姓的主動行為。從商鞅變法算起,秦法在六代國君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保證了秦的強大,并最終使得秦一統(tǒng)華夏。
“無為”實則大有為
漢朝政治制度事實上就是秦朝制度的復制、改進版本,是為“漢承秦制”。漢朝官方之所以在宣傳上強調“黃老之學”、“無為而治”,除了技術上的區(qū)別之外,恐怕也有“政治正確”的考慮——需要和前朝加以區(qū)分。相對于秦制,漢制最大的改變在于更加“務實”。一方面,《漢律》對比《秦律》其實要更加嚴苛;而另一方面,面對現(xiàn)實,中央政府做出了大量妥協(xié)。
西漢的國家體制可以算是“一國兩制”:函谷關以西,延續(xù)秦朝的郡縣制,是中央政府的自留地;函谷關以東,則恢復了周代的封國制,最初的封王們擁有封地官員的任免權、收稅權甚至自己的武裝力量。
但是中央政府從未停止過削弱封王的權力,雖然說中間出了“七國之亂”,逼著漢景帝不得已殺了晁錯,但這在某種程度上反倒加速了中央政府削藩的步伐。經(jīng)過數(shù)次削藩,函谷關以東封國,在行政級別上降到了郡一級,面積也大為減少。封國內官員的任免權、司法權和商業(yè)稅等權力,也逐一被中央政府收回。
到了漢文帝時期,距離漢朝開國已有數(shù)十年,當初跟隨漢高祖的元老大臣,因為年齡的關系,影響力開始逐漸減弱。于是漢文帝抓住這個時間窗口,軟硬兼施,把老一代勛貴紛紛遷出長安,這樣就擺脫了元老大臣的掣肘。
在經(jīng)濟層面,漢帝國在立國初期沒有像秦朝那樣,大量上馬大型基建工程,而是通過減少財政支出降低了稅率。漢高祖劉邦時期,農業(yè)稅的稅率是“十五取一”,文景兩代皇帝時,進一步降到了“三十取一”,這也是中國古代稅率最低的時期。在漢文帝時代,又進一步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使得商品跨地區(qū)運輸不再需要的政府批文。
低稅率政策使百姓收益,但最大的獲利者還是地方上的豪強,這些富人迅速積累起大量財富,開始瘋狂兼并土地,甚至私自鑄錢。文景兩代對于豪強的打壓其實也從未中斷過,雖然不能徹底扭轉局勢,但也緩解了社會過度兩級分化的問題。這一松一緊兩手政策,最終使得漢帝國的中產階層,也就是“良家子”得以壯大。在后來漢武帝北逐匈奴的戰(zhàn)爭中,漢軍的主力正是來自這一階層。
在社會階層問題上,漢制在延續(xù)了秦朝的平民受爵制度,但讓爵位制度從不得世襲變成可以降級世襲(比如父輩是侯爵,到子輩就是伯爵,到孫輩便是子爵),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也被重新劃分。如此一來,漢朝的“階層固化”問題雖然比秦朝嚴重,但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固化的確使其社會穩(wěn)定性高于統(tǒng)一之后的秦朝。
此外,漢初的幾代皇帝對自身需求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劉邦修建了未央宮和長樂宮以后,文景兩代對位于長安的首都圈基本再無改動。尤其是漢文帝,宮室、儀仗、車輛幾乎都繼承自上一代。

綜上所述,漢初幾代皇帝發(fā)“無為”并不等于“不為”,相反,數(shù)十年的看似“無為”實則大有為,最終造就了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守十方可得之六七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是“漢承秦制”,為什么漢朝延續(xù)了400余年,而秦朝卻二世而亡呢?
從權力層級來看,秦國家權力一直延伸到鄉(xiāng)村一級,這一制度最大限度的保證了國家對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但隨著疆域的擴大,秦制的運行成本急劇上升,在農業(yè)時代,要在340萬平方公里(秦朝的國土面積)且地形多種多樣的土地上延續(xù)如此嚴密的管理體系,其“投入產出比”必然是非常低下的。這也是導致秦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社會階層來看,秦人最大限度的追求“扁平化”。除了前述的爵位無世襲之外,秦的社會構成不存在“士、農、工、商”這樣的等級區(qū)分,君王和官員以外的其他國民統(tǒng)稱為“黔首”。而隨著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結束,一系列的問題也隨之顯現(xiàn),六國貴族的利益在新的體制下變得難以為繼,這是比滅國更讓他們難以接受的。此外,扁平化的社會階層劃分,以及以功受爵制度所表現(xiàn)出的社會活力,在和平時期就顯得過于“熾烈”了。這也成了導致秦朝滅亡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位于陜西臨潼的西入口的秦統(tǒng)一雕塑群視覺中國資料
漢帝國建立之前,大秦帝國用了十四年時間打擊地方豪強,興建遍布全國的弛道以及水利設施,將戰(zhàn)國時期秦、趙、燕三國的長城重新維修整合,還把各地大族、富戶大部分遷到“關中首都圈”,讓這里的經(jīng)濟總量能對其他地區(qū)形成絕對優(yōu)勢。如此一番功夫,一個統(tǒng)一國家的基本硬件已經(jīng)完全建成。但與此同時,秦王朝與既得利益階層的矛盾徹底爆發(fā),這是秦朝滅亡的直接誘因。
相比之下,漢朝的政策看似“無為”,但其實也一直在變,其政策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原因有三:首先,秦的教訓讓漢初幾代帝王都認識到,壓制既得利益集團必須為之,但如果引發(fā)高烈度的沖突,將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所以,在維系基本盤穩(wěn)固的前提下,漢朝對貴族集團做出了大量妥協(xié),以緩和前朝時期中央政府與地方豪強間的矛盾。
其次,秦朝十四年的基礎建設以及對貴族階層的高壓政策,已經(jīng)固化了大一統(tǒng)的基本格局,漢帝國則充分接受了這一來自前朝的“饋贈”。
再次,無論漢初如何內憂外患,但國家面臨的環(huán)境終歸沒有戰(zhàn)國時期中原諸侯國那么嚴酷,天下一統(tǒng),自然不會再有諸侯國之間的征伐,而帝國龐大的體量,也可以讓國家有余力消化來自北方匈奴的襲擾。內外壓力都不大,就給政策推進在時間上留出了足夠的余量,無需短時間內一蹴而就。如此一來,改革的過程就被分解得非常細碎,相應的也就不會遭遇太大的反彈。可以說,是時間稀釋掉了改革的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漢初幾代帝王在政策上的延續(xù)性,是漢帝國這種漸變式改革得以實現(xiàn)的根本保證。某種程度上說,秦漢應當被視作是一體,中國的大一統(tǒng)始于秦,成于漢。在漢帝國以“進三退二”的模式(秦進三,漢初退二),最終完成了前朝想做但未做成的事情。
從古至今,圍繞利益劃分所做的改革,所遵循的大多都是“守十方可得之六七”的規(guī)律。任何人在利益受損后都必然會反彈,多數(shù)改革最終也都會有所回調。今天做到了十,后面才有“進三退二”的空間,最后剩下的“六、七分”才是最終成果。說到底,改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