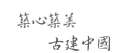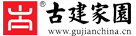黑格爾認(rèn)為:“戲劇是一個(gè)已經(jīng)開化的民族生活的產(chǎn)品。”戲劇的產(chǎn)生,需要“人的目的、矛盾和命運(yùn)就必須已經(jīng)達(dá)到自由的自覺性而且受過某種方式的文化教養(yǎng),而這只有在一個(gè)民族的歷史發(fā)展的中期和晚期才有可能”。他所說的戲劇,是歐洲中世紀(jì)之前與之后的戲劇。他的歷史主義方法,體現(xiàn)在把不同的藝術(shù)類型——美術(shù)、音樂、文學(xué),以及文學(xué)中的史詩(shī)、抒情詩(shī)和戲劇與人類的“開化”階段聯(lián)系起來,例如,戲劇需要人從神的蒙蔽之下覺醒過來,對(duì)自身的“目的、矛盾和命運(yùn)”有充分的自覺,并因此而獲得行動(dòng)的“自由”。
對(duì)黑格爾來說,在馬洛和莎士比亞之前,或者更準(zhǔn)確地說,在但丁之前的歐洲中世紀(jì)不存在戲劇。根據(jù)同樣的理由,他認(rèn)為直到他談?wù)撨@個(gè)問題時(shí),東方還沒有戲劇,即使中國(guó)和印度也只有戲劇的萌芽。把人的精神解放、人對(duì)自身的信仰當(dāng)作戲劇產(chǎn)生的必要前提,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和一個(gè)非常重要的思想!上個(gè)世紀(jì)的戲劇發(fā)展史再一次證明了它的正確。當(dāng)對(duì)于馬洛和莎士比亞來說的“新世紀(jì)”已經(jīng)變得足夠陳舊與衰老的時(shí)候,當(dāng)西方人對(duì)從神的庇護(hù)與看守下解放出來的人的命運(yùn)與價(jià)值產(chǎn)生了普遍懷疑的時(shí)候,黑格爾所說的戲劇,作為一種文體,便坍塌了,出現(xiàn)了被漢斯-蒂斯·雷曼(Hans-ThiesLehmann)教授稱為“PostdramaticTheatre”(后戲劇劇場(chǎng))的新戲劇文體。
這種新戲劇文體從被黑格爾無視的歐洲中世紀(jì)戲劇和被黑格爾認(rèn)為并非戲劇的東方戲劇中汲取了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作靈感與藝術(shù)資源。這種新戲劇文體的出現(xiàn)提醒我們思考:如果歐洲中世紀(jì)也存在過故事表演,這種被黑格爾所無視的“故事表演”具有什么與馬洛和莎士比亞所不同的戲劇文體呢?而在過去,我們一直把它當(dāng)作莎士比亞戲劇文體的不發(fā)達(dá)階段,而不認(rèn)為它會(huì)是屬于被馬洛和莎士比亞們拋棄了的神學(xué)世界觀的另一種戲劇文體。如果說,歐洲中世紀(jì)的戲劇確實(shí)不夠發(fā)達(dá),至少?zèng)]有像被黑格爾認(rèn)為僅有戲劇萌芽的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那樣擁有大量卓越的戲劇文本,那么,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重新考慮黑格爾的論斷,把關(guān)漢卿、湯顯祖?zhèn)兊膫ゴ笞髌罚部醋饔刹煌隈R洛、莎士比亞的世界觀所決定的不同的戲劇文體呢?而在過去幾十年里,它們是一直被中國(guó)戲劇學(xué)者當(dāng)作跟莎士比亞一樣的戲劇文體來闡釋的,莎士比亞戲劇分場(chǎng)不分幕的時(shí)空處理方式被用來強(qiáng)化了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使用同一種文體創(chuàng)作的想象。
重要的問題是,關(guān)漢卿、湯顯祖?zhèn)兊膽騽『蜌W洲馬洛、莎士比亞之前的戲劇是不是相通的?是不是共同的文體?根據(jù)黑格爾的看法,它們都具有“相信實(shí)體性的力量只有一種,它在統(tǒng)治著世間被制造出來的一切人物,而且以毫不留情的幻變無常的方式?jīng)Q定著一切人物的命運(yùn)”的意識(shí)形態(tài)特征,這樣“相信實(shí)體性的力量只有一種”的時(shí)代,我稱之為“集體信仰時(shí)代”。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這個(gè)時(shí)代都缺乏馬洛和莎士比亞戲劇“所需要的個(gè)人動(dòng)作的辯護(hù)理由和返躬內(nèi)省的主體性”。馬洛和莎士比亞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邁入了個(gè)人主義時(shí)代。
——呂效平:《〈帖木兒大帝〉〈世人〉和〈郭布達(dá)克〉——我們?yōu)槭裁匆l(fā)〈帖木兒大帝〉》,原載《戲劇與影視評(píng)論》2017年第2期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