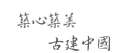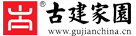在語(yǔ)言產(chǎn)生之前,人類就開始在洞中的石壁上作畫,各種各樣的圖案所表達(dá)的意義凝練卻也極具想象力,在歷史的長(zhǎng)河中超越語(yǔ)言文字的存在,在特定的時(shí)期和特定的人群中體現(xiàn)著不同尋常的含義。
在歐洲大陸,生命曾被屠戮,土地曾被焚盡,家徽卻永不被玷污。百年來(lái),一個(gè)家族的歷史興旺被濃縮成圖案刻成家徽,家徽又被刻印在大到建筑、小到餐巾的物件上,以圖案本身沉默卻龐大的敘事方式和每一位觀者交流,這些圖案所講述的故事旁征博引,從法國(guó)的雄雞、英國(guó)的獅子到德國(guó)的雄鷹,好像敘述者的聲音也被壓扁,以完全不借助文字的形式表達(dá)。
如果說(shuō)家徽里的圖案是一個(gè)家族的故事,建筑風(fēng)格本身的圖案元素則是整整一個(gè)時(shí)代、一段文明的故事。線條圓潤(rùn)飽滿、常見螺旋、貝殼、山石圖案的洛可可是歐洲最為人熟知的裝飾風(fēng)格。彼時(shí),歐洲經(jīng)濟(jì)正發(fā)展得生機(jī)勃勃,洛可可風(fēng)格將城市裝點(diǎn)得如同奶油蛋糕一般甜美。在洛可可式圖案的勾勒下,在乘著馬車可及的郊外,花團(tuán)錦簇,綠草如茵,世界被裝點(diǎn)出夢(mèng)幻的痕跡。織染面料上總能見到精致的蘭花與薔薇,那是18世紀(jì)法國(guó)人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的如煙似霧蒸騰的愉悅。
傳說(shuō)上帝為了阻止通天塔建成,給予了人類不同語(yǔ)言和文字以生隔閡。而經(jīng)由圖案?jìng)鬟_(dá)的意義,則脫離了語(yǔ)言,它所喚醒和溝通的是一種更為純粹的感官體驗(yàn)。留學(xué)生石靜最初便是通過(guò)一塊茶巾了解日本精神,那上面是日本最常見的松鶴圖案,淺黃的布面更平添了一股疏離清淡,顯示出日本沉郁的性格。石靜說(shuō):“我始終無(wú)法理解日語(yǔ)中那些描述情緒、難以準(zhǔn)確界定和翻譯的詞匯,然而看到這塊茶巾上的圖案,我卻瞬間明白了,那種更偏向冷色調(diào),仿佛雨后冷風(fēng)一樣寂寥的感受。”
也許正是由于圖案本身的創(chuàng)造早于文字,我們更容易從圖案中找到各個(gè)文明的共同點(diǎn),就像樹木象征生命的初始意義,人們對(duì)于生命長(zhǎng)過(guò)自身的物種總會(huì)保持本能的憧憬與熱愛,許多文明都可見“生命樹”的意象。人們將其作為本民族的“圣樹”,對(duì)它和它所象征的生命繁衍頂禮膜拜。而后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本能把這種美好祝愿抽象成線條、花紋和圖案,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蓮花、棗椰、忍冬、茛苕燈都被融入其中,它們卷曲的經(jīng)絡(luò)延伸出對(duì)稱的漩渦圖案。人類在自然中學(xué)會(huì)了生存的方式和意義,從植物身上理解了對(duì)稱、延展、色彩這樣的美學(xué)意義,而在這一系列的學(xué)習(xí)和應(yīng)用中,人真正成為了人。
如果說(shuō)對(duì)于生命的熱愛是人類共性,對(duì)于死亡的贊美則是拉丁美洲文化獨(dú)特的標(biāo)示。無(wú)論是誰(shuí),凡是知道墨西哥亡靈節(jié)的,都會(huì)對(duì)那些骷髏圖案印象深刻。不像其他地域的陰暗可悲,亡靈節(jié)上的骷髏總是與鮮花、蝴蝶這樣生機(jī)勃勃的意象一起出現(xiàn)。在那些骷髏面具下,是活生生的人、表情鮮活的臉。“對(duì)墨西哥人來(lái)說(shuō),亡靈節(jié)的意義正是由這種生命與死亡界限模糊的圖案呈現(xiàn)。”導(dǎo)游卡洛斯說(shuō)。墨西哥籍的諾貝爾獎(jiǎng)得主帕斯曾寫過(guò):“死亡其實(shí)是生命的回照。如果死得毫無(wú)意義,那么,其生必定也是如此。”根植于印第安文化的墨西哥人對(duì)此深信不疑,所以才會(huì)在10月底到11月初的兩天,為幼兒和成人的亡靈舉行盛大慶典。在那些鮮花簇?fù)聿实w舞的骷髏面具之下,生命與死亡真正意義上界限不分,加西亞·馬爾克斯描述的帶有腐爛花朵香味的拉丁美洲,在陽(yáng)光下,帶著骷髏面具翩翩起舞。
文字筑起的高墻被圖案打破,屬于某種文化的特有圖案高度濃縮地呈現(xiàn)了內(nèi)在的骨骼經(jīng)絡(luò),激活了眼睛,沖破了靈魂的框架,讓人們?cè)诟泄僦弥辛鬟B忘返。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