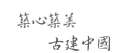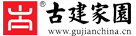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乃至其后的歷史時期,亞歐大陸各文明區(qū)域的不同文化成果幾乎都是通過天山完成交流的。其中,因貿(mào)易關(guān)系在進入該地區(qū)后,被逐步接受或擴大影響。這樣的文化交流從未停下過腳步,而是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東亞文明核心區(qū)——中國。反向也同樣如此,來自東方中國的文化和絲綢等諸多珍貴時尚高檔物品也源源不絕地經(jīng)天山向西運送。
從事商貿(mào)活動的并不只限于綠洲居民,草原游牧人群也非常重視商貿(mào)。二者都與東亞中國、南亞印度、中亞各綠洲、伊朗高原、西亞兩河流域以及非洲、歐洲來往密切。雖然如此,天山并沒有隔絕山南山北的各種溝通來往。中國古代文獻中有大量關(guān)于塞種(斯基泰)、匈奴、突厥等游牧人群和西域諸綠洲小國進行各類活動的情況。作為中亞兩種自然環(huán)境天然界線的天山山脈,對山北的游牧民族來說起到了將其政治勢力推向東方和南方的作用,而對山南的綠洲民族來說則是通向東方、北方進行貿(mào)易的道路。

此外,天山山脈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作用,那就是引導(dǎo)草原游牧人群流入綠洲,并使其轉(zhuǎn)變?yōu)榫G洲農(nóng)業(yè)居民的作用。從天山北部遷入綠洲地帶的游牧人群會轉(zhuǎn)入定居的農(nóng)耕生活,而隔著這座山脈游牧的人群卻鮮有改變。天山在相當(dāng)長的歷史時段里都是綠洲與游牧兩種社會生活形態(tài)的分界。
在天山山脈的庇護下,數(shù)千年來亞歐大陸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農(nóng)耕、游牧兩種社會生活形態(tài)的交互影響得以持續(xù)。實際上,亞歐大陸東西交往以及中亞南北往來都依賴于天山,它是古代亞歐大陸所有交通通道中最大也是重要的樞紐型“十字路口”。
沿天山山脈展開的亞洲腹地作為連接亞歐東西方的通道,還可以說是世界歷史發(fā)展的關(guān)鍵區(qū)域。這個區(qū)域猶如人體動脈把古代的中國、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錫爾河地區(qū)、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等連接起來,并使其相互依存地發(fā)展起來。另外,它還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橋梁。出現(xiàn)在這個地區(qū)的來自不同文明區(qū)域的文化,或經(jīng)民族遷移(包括戰(zhàn)爭),或依靠商隊等傳播至東西方各地。所有這些在影響其他區(qū)域文化的同時,也不斷接受各種不同的文化而改變著自身。
天命觀與天山
中國古代哲學(xué)中把天當(dāng)作神,天能致命于人,決定人類命數(shù)。“天命”說早在商代就已流行,迄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流傳歷史。《小戴禮·表記篇》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從古器物發(fā)掘中所見到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來看,“受命于天”的刻辭不只一次出現(xiàn)。如大盂鼎銘文:“王若曰: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斷是康王時期,明確表達了天命觀。當(dāng)然,與天命觀關(guān)聯(lián)的還有早期中國的天地崇拜觀念。
產(chǎn)生于古代中國的天命思想,在絲綢之路這樣的亞歐大陸全區(qū)域文化傳播交流吸收的歷史過程中,很早就影響到了西域。在天命觀念的影響下,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帶很早就出現(xiàn)了“天”的崇拜觀念,《史記》《漢書》等歷史文獻中記載的諸如“孤涂撐犁單于”(大天子)一類的名稱數(shù)量極多。

天山這個名稱,最早見于文字記載,是在《史記》卷110《匈奴列傳》中:“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得胡首虜萬余級而返。”《漢書》卷六《武帝紀》,把這一歷史事件的發(fā)生時間定于天寒二年(公元前99年)夏五月。
天山還有別的名字。魏王泰《括地志》記載:“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曼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隋書》卷84《西突厥傳》記載:“(處羅可汗)棄妻子,將左右數(shù)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東,保時羅曼山”;《舊唐書》卷四《地理志》伊州伊吾縣條目中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羅曼山”;敦煌文書《沙洲伊州地志殘卷》伊州柔遠縣條目記載:“時羅曼山縣北四十里。按《西域傳》,即天山。綿亙數(shù)千里”;此外,還有“祁連山”、“貪漢山”等名。
析羅曼山、折羅曼山、時羅曼山、祁連山、貪漢山、騰格里山等天山之名都是音譯,均是古代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天”之詞“Tangri”,即天命觀中受命于天之天,是中國古代文化精髓在西域產(chǎn)生影響的具體表現(xiàn)與象征。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