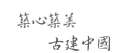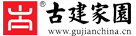1528年,當神圣羅馬皇帝查爾斯五世在西班牙第一次看到一種名為“烏拉瑪”(Ulama)的球賽時,如同其他歐洲人一樣,他對這種新鮮的游戲感到不可思議。這次比賽的場景恰好被一位德國人畫了下來,使我們得以一窺古代中美洲球賽的激情和神秘。
烏拉瑪是阿茲特克人對這種球賽的稱呼,它更早的名字我們已經無從知曉。目前的考古發現證明,最晚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就已經出現了這種球賽。在一個名為Paso de la Amada(西班牙語,意為“愛的階梯”)的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由泥土壘成的球場,此外還有一些表現球賽場景的陶塑。
到了奧爾梅克時期,球賽變得流行并且重要,大量的比賽用球在祭祀水坑中被發現,著名的巨石頭像被雕刻為球員的形象。古代美洲最大的城市特奧提瓦坎中充斥著大量球賽的壁畫,而瑪雅文明中關于球賽的石雕和銘文更是數不勝數,幾乎在任何一個瑪雅城市,都能發現一個或數個球場。

這種比賽用球由橡膠制成,是實心的,目前共發現大約100個大小不一、重約1.5—3.5千克不等的比賽用球。由于球比較重,球員必須穿戴護具。根據考古發現,球員一般在頭部、腰部、腿部戴有護具。護具一般為木質,但在一些遺址中,出土過石質護具。比如,大英博物館就藏有一件青石護具,不過學者們認為,這是用于祭祀活動的。
球場平面形狀為大寫的“I”形,中間的長廊以及兩端的長方形區域就是比賽場地,兩側為斜坡狀臺基,斜坡上部往往還有若干個環狀或者動物石雕。此外,在一些球場的長廊內,還會設置三個標志柱。有時,臺基上還有建筑或者階梯,用于觀賽人群的聚集和舉行相關儀式。球場大小不一,目前發現最大的球場是奇琴伊察(Chichen Itza)的大球場,長96米,寬30.4米。
球賽是如何進行的,目前沒有明確的資料記載,學者們也爭論不一。一般認為,根據球場大小不同,共有2—8名球員參賽。參賽球員用胯部將橡膠球保持在空中運動,不能落到球場中間的長廊內,但可以落到兩側的斜坡上。長廊兩端的方形區域為得分區,類似美式橄欖球的達陣區,將球觸到對方得分區的地面即算是己方球隊得分。
另外,還有研究者認為,將球穿過球場斜坡上設置的圓環,或是觸碰到上面一些石質雕件(如科潘球場上豎立的鸚鵡頭)和長廊中的標志柱,都可以算得分。除了用胯部以外,也有研究者認為,手肘、腿部、腳部都可以觸球,甚至可以用木棍擊球,《博基亞抄本》(Codex Borgia)中就描繪了這樣的場景。
社會復雜化的工具
球場是古代中美洲人民娛樂的重要場所,在一些出土的陶塑上,可以看到人群在球場旁邊吶喊圍觀的場景。但球賽不僅僅是娛樂活動,還包含了其他的內容,如賭博,這在文獻和考古資料中都能得到體現。
在《博基亞抄本》中有一幅修齊奎扎爾(Xochiquetzal)和她的丈夫馬奎修齊特爾(Macuilxochitl)對坐的圖像。修齊奎扎爾是阿茲特克的一位女神,主管美麗、豐產、音樂、舞蹈、手工藝等,她的丈夫馬奎修齊特爾則主管藝術、游戲、賭博、鮮花等,他們夫妻二人是阿茲特克人游戲和賭博的守護神。
在這幅圖像上,修齊奎扎爾坐在凳子上對著丈夫揮舞著雙手,情緒高漲,似乎準備從板凳上跳起來。她的丈夫馬奎修齊特爾則左手叉腰,右手高舉,正和妻子爭辯。這應當是表現了夫妻二人正在進行游戲或者賭博的場景。二人的正中間繪制了一個黑色的類似九宮格的圖案,這個圖案就是一種具有賭博性質的游戲。而在黑色圖案的正上方,赫然用繩索懸掛著一個橡膠球。
在洪都拉斯科潘遺址,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在大球場的地下發現了一座更早時期的球場。在早期球場的神廟中,考古學家在地面上同樣發現了與《博基亞抄本》中幾乎一樣的類似九宮格的圖案,這證實了球賽與賭博的密切關系。
有學者認為,球賽無論是為了娛樂還是賭博,都是社會復雜化進程中非常重要的工具。比如,約翰克拉克等人就認為,舉辦或者贊助球賽是那些雄心勃勃的財富積累者獲得威望、攫取社會權力的重要途徑。而在賭博中,一些人失去了財產甚至人身自由,成為依附于他人的奴仆。在最早出現球場的“愛的階梯”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一系列社會復雜化的證據,包括大型公共房屋的出現,陶器中用于宴饗的器物尤其是酒器數量的劇增等。而在奧爾梅克文明時期,著名的巨石頭像一般被認為是裝扮成球員的國王形象。

儀式功能的強化
僅僅是娛樂或是賭博遠遠不能涵蓋球賽的意義,事實上,球賽更多的是儀式的一部分,尤其是越到晚期,儀式的功能愈加凸顯。特別是在古典瑪雅時期,這種儀式功能在雕刻、銘文、壁畫和陶器彩繪中得到大量體現。
球場具有非常明顯的象征意義。瑪雅神話《波波烏》(Popol Vuh)里記載了玉米神和英雄雙兄弟在球場游戲驚擾了西瓦爾巴的死神,被召喚到地獄的故事。書中描述的球場位于地獄西瓦爾巴的上方,是人間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同樣,在科潘球場,考古學家發現了三個石質標志柱,呈平面形狀近圓形。在石塊上雕刻了“亞”字形的方框,方框內是兩名球員正在進行球賽的場景。
這種“亞”字形的雕刻大量發現于壁畫和雕刻之中,象征了大地的裂縫和地下世界的出入口。玉米神一般就從這個“亞”字形的裂縫中重生,如在桑巴特洛遺址出土的壁畫中,玉米神就在大地怪獸的裂縫中載歌載舞等待重生。這種“亞”字形的圖案雕刻最早可追溯至奧爾梅克時期,祖先神往往伴隨著云霧現身其間。因此,科潘球場的這三個標志柱在瑪雅人看來就是人間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球場具有連接地下世界的象征意義不言而喻。
球賽一般伴隨著祭祀和犧牲。科潘遺址大廣場上出土的4號祭壇表現的就是一個被繩索捆綁的比賽用球形象,用于祭祀。上部有一刻槽,學者們一般認為,是用來引流犧牲的鮮血。與科潘4號祭壇類似,提卡爾遺址8號祭壇同樣表現了一個比賽用球,上面雕刻了兩個被繩索捆綁的犧牲,從他們的頭飾來看,身份并不低。在亞斯奇蘭遺址的2號象形文字臺階上,雕刻了一場特別的“比賽”。亞斯奇蘭的鳥豹王裝扮成玉米神正準備擊打從臺階上滾落下來的球,球內雕刻的就是一個被捆綁的犧牲。
類似的場景在雕刻、壁畫和彩繪中比比皆是。但是,考古發現中并未找到階梯狀的球場。考古學家認為,這只是對比賽結束后祭祀場景的描繪,這在大量的雕刻銘文中可以得到佐證。由于比球場更具展示祭祀過程的視覺效果,瑪雅人選擇在階梯上進行殺牲獻祭的儀式。
基于祭祀活動的重要性,球場甚至被稱作“六階之地”(瑪雅語Wak-Eb),意指有六級臺階的祭祀場所。有些“六階之地”甚至開始模仿真實的球場,設置了三個標志柱,如科潘遺址22號神廟的南部小廣場。與此同時,銘文中開始出現大量的以臺階表示球場的象形文字。這些跡象均表明,在古典瑪雅時期,球場的象征意義大于實用意義,球賽越來越偏向儀式化,祭祀的功能愈加凸顯。
在球賽中殺俘虜祭祀是瑪雅人的風俗,那就意味著球賽會經常與戰爭聯系到一起。在一些銘文中,有一種被稱作“三征服之地”(瑪雅語Ox-Ahal-Eb)的球場,有學者認為這樣的球場就像是一座戰爭紀念碑。在納蘭霍遺址出土過一件石雕,記述了王國被南部的城邦卡拉克爾打敗的故事,銘文上寫著納蘭霍的國王“在三征服之地進行球賽”。
科潘的象形文字臺階上有兩個關于球場的描述詞,一個是“蝙蝠之屋球場”,另一個就是“三征服臺階”。蝙蝠之屋是關押戰俘的場所,《波波烏》里記載英雄雙兄弟就曾經被死神關在蝙蝠之屋。巧合的是,在象形文字臺階的上方神廟中,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與戰爭之神——特拉洛克相關的雕刻。這些證據足以表明球賽和戰爭的密切聯系,也不由得讓我們回想起《波波烏》里,球賽最初就是英雄雙兄弟和地獄死神之間的戰爭。
從墨西哥灣的奧爾梅克文明、墨西哥中部的特奧提瓦坎和阿茲特克文明,到奧哈卡谷地的薩波特克以及南部的瑪雅文明都對這種球賽癡迷至極。因為它不僅僅是一種令人血脈僨張的體育運動,更是融合了多種社會和儀式功能,加強文化認同的工具。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當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以后,為了便于統治,他們以球賽過于危險為名,取締了這項活動。
 手機版|
手機版|

 二維碼|
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