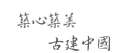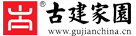中國古代是一個(gè)有情調(diào)的社會(huì),但他們并不擅長這塊。在很多的浪漫主義作品中,許多理應(yīng)是調(diào)情的情節(jié)多半表現(xiàn)為調(diào)戲,后人看來更多的為調(diào)戲。作者讀圣賢書,寫出這些浪漫作品,大概原因有二:一是這些在今人看來經(jīng)典的作品,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評判體系中是通俗文學(xué),有為迎合受眾而蓄意增加淫樂粗俗橋段之嫌;二是古代社會(huì)完全由男權(quán)主宰,男性擁有話語權(quán),掌握著定性某種行為的權(quán)力。比如清代,女性被調(diào)戲,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jià)才能換回法律對騷擾者的制裁。

殺人牌坊
清代系少數(shù)民族執(zhí)政,民間文化仍然以傳統(tǒng)儒家文化為主,社會(huì)文化主題以家庭為核心,提倡婦女守貞持節(jié)。社會(huì)文化對女性貞潔的重視、制度對貞潔的推崇和維護(hù),增強(qiáng)了女性在受到性騷擾、性侵害時(shí)的羞恥感。
清朝入關(guān)之初,為了維護(hù)社會(huì)秩序,傾向于從嚴(yán)處置。性犯罪案件按照“威逼人致死律”,處斬刑。按照《大清律例》,“若因行奸為盜,而威逼致死者,斬。監(jiān)候。奸不論已成與未成,盜不論得財(cái)與不得財(cái)。”例如,《明清檔案》載順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廿四日案例,直隸呂名全窺見侄女呂大姐獨(dú)居室內(nèi),入室摟抱并扯退呂大姐衣褲意欲強(qiáng)奸,呂大姐高聲呼喊,被其兄呂化聽聞,趕回家中,呂名全逃跑。呂大姐含羞愧恨于次日清晨自縊。呂名全擬合依“威逼致死”處斬監(jiān)候。清律沿襲明律,“威逼致死”的立法意是嚴(yán)懲豪強(qiáng)暴徒,如果是強(qiáng)奸未遂而適用此法,實(shí)際上量刑偏重。
隨著清代政局逐漸穩(wěn)定,關(guān)于法律的適用也出現(xiàn)了變動(dòng)。到了雍正皇帝時(shí),強(qiáng)奸未遂受害人羞憤自盡的,雖說后果嚴(yán)重,但將受害婦女死亡作為量刑要件被認(rèn)為對罪犯太過嚴(yán)苛,遂于十一年(1733年)增添一條律文:“強(qiáng)奸未成,或但經(jīng)調(diào)戲,本婦即羞忿自盡這,俱擬絞監(jiān)候。”(此條不適用于強(qiáng)奸服制內(nèi)親屬)同樣是死罪,“絞”留全尸,對于把“死無全尸”當(dāng)作詛咒的古代中國人而言,與身首異處的“斬”相比是更輕的情節(jié)。
雍正皇帝的這次修法引發(fā)了一些歧義,原本婦女遭言語調(diào)戲并不一定非要以死明志,修法之后,“羞忿自盡”成為罪犯被處以絞刑的前提要件之一,女性不得不以生命為代價(jià)作為被侵犯的自我人格的補(bǔ)全措施。白璧無瑕的貞潔已經(jīng)通過法律深入清代女性理想設(shè)定。《江西省情實(shí)重囚招冊》記載,雍正十二年(1734年)趙情三與侄子趙石一在一個(gè)院子里居住,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趙情三見侄子赴省城未歸,侄媳婦喻氏在房中和小姑子五妹作伴。半夜,趙情三掇開喻氏房門,拉扯喻氏的手,喻氏高呼,趙情三逃走。次日,喻氏向婆婆哭訴,婆婆沈氏向族內(nèi)房長請求處置趙情三,趙情三謊稱與喻氏連夜通奸,你情我愿,并不屬于騷擾。喻氏羞忿自殺,趙情三因?yàn)榍址阜苾?nèi)親屬,被處斬刑。性騷擾本就很難保留證據(jù),女性缺乏話語權(quán),一旦被反誣,只能以死換取法律對罪犯的制裁并自證清白。
到了乾隆朝,國家為了強(qiáng)化貞潔觀念,旌表自盡婦女。大清律例中有“強(qiáng)奸不從,以致身死之烈婦。照節(jié)婦例旌表,地方官給銀三十兩,聽本家建坊”。也就是說,受害婦女以死明志之后不僅可以得到一塊貞潔牌坊,家屬還能得到旌表銀子和埋葬銀子共計(jì)約五十兩,朝鮮人俞彥述在《燕京雜識》記述當(dāng)時(shí)清朝民眾生活狀況稱:“或云以人一年之食,多不過銀子三兩云。”五十兩銀子對于清代平民的意義可想而知。
乾隆時(shí)期,“婦女經(jīng)調(diào)戲羞忿自盡”的案件特別多,經(jīng)濟(jì)因素的加入使得性騷擾問題變得更加復(fù)雜。清人方浚師在《蕉軒隨錄·續(xù)錄》中引用《律例條辯》稱,男性調(diào)戲女性,“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騰穢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手法不同,同理女性自盡的原因也存在不同情況,“或怒,或慚,或邪染,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鳴貞,或別有他顧而飾詞誣陷。”這種敘述代表了士大夫階層男性的普遍憂慮,對于那些有可能本來就有輕生念頭,或是為了獲得旌表的女性,受調(diào)戲不過是自盡的借口,而調(diào)戲者卻要因此被斬殺絞死,實(shí)在不公平。乾隆朝的另一處立法修改,將強(qiáng)奸未遂從斬改為絞監(jiān)候或杖一百,徒三年,對性犯罪進(jìn)一步表現(xiàn)出寬容。在行政方面,強(qiáng)奸未遂受害婦女自盡的,予以旌表;強(qiáng)奸既遂的,婦女自盡則不予旌表,充分表明清政府并不在意婦女的人身權(quán)益,在乎的只是觀念上的貞潔。
籬笆,女人,騷擾犯
清代大量女則女訓(xùn)流行民間,強(qiáng)調(diào)男女授受不親,在生活區(qū)域也要區(qū)分男女活動(dòng)空間。但這種物理上的隔閡并不容易實(shí)現(xiàn),就北京一城而言,十八世紀(jì)已經(jīng)有超過五十萬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四萬五千人,住房空間狹小,很難實(shí)現(xiàn)生活區(qū)劃分,甚至不得不“同床共枕”。《內(nèi)務(wù)府來文·刑罰類》記載了一則控告親兄弟的案例。受害人二妞稱家中兩間房子,父親得了痰癥不能起炕,二妞和父親睡一張炕,哥哥二達(dá)子睡木床,二妞指控二達(dá)子對她進(jìn)行性騷擾。慎刑司對這個(gè)案件的判決是“二達(dá)子母死父病,不善撫恤伊妹,屢與爭吵,以致伊妹妄控,照不應(yīng)重律,杖八十”。這個(gè)判決的奇怪之處在于,既然定性二妞誣告,“不善撫恤”和兄妹爭吵應(yīng)該不至于被杖打八十,二達(dá)子雖然受罰,卻無罪名,性騷擾的指控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城市居民同床共枕,農(nóng)村夜不閉戶也容易滋生性犯罪案件。《內(nèi)閣題本刑克·婚姻奸情類》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十四日案件。甘肅如寧縣村民杜潤先與妻子外出探親,家中留婢女三姐一人看家,找鄰人魏榮的獨(dú)女足姐伴宿。同村趙雨對三姐時(shí)起奸淫之意,是夜?jié)撊耄愀呗暫艚校w雨害怕他人聽見,毆傷三姐,強(qiáng)奸未遂。此時(shí)足姐驚醒喊叫,被趙雨用刀扎傷,魏榮趕來查看情況,趙雨棄刀逃跑。依照大清律例,只有在出現(xiàn)死傷的情況下,才適用于“夜無故入人家內(nèi)者,杖八十”條款,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出清代進(jìn)入他人家門并不是一件難事。趙雨夜入人家,毆傷他人,又涉及奸情,最后以“強(qiáng)奸執(zhí)持兇器戮傷本婦及拘捕致傷旁人”被判絞監(jiān)候,這是一個(gè)強(qiáng)奸附帶故意傷害數(shù)罪并罰的案件。三姐沒有以死明志,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個(gè)案件牽連他人,如果是獨(dú)居,大概也要添作牌坊才能換來對罪犯的法律制裁。
另外清代女性喜歡串門。朝鮮使者李坤在《見聞雜記》中記載,“無貴賤老少皆朱唇粉面……婦女緞衣粉面頭花耳珰,不治女紅,倚門治容。”《順義縣志》也記載當(dāng)?shù)匾恍D女“臉不洗,串街坊,抱著人家孩子洗風(fēng)狂,人家炒菜他聞香”。另一名朝鮮使者李宜顯在《陶谷集·庚子燕行雜識》中發(fā)現(xiàn)清代婦女“與之雜坐、吸煙、接膝交手而不以為嫌”。不僅小家小戶如此,中上人家的女性也喜歡倚門觀望。可見,女性出門在清代是一件頗為普遍的事情。
由于缺乏實(shí)現(xiàn)性別隔離的理想條件,清代多數(shù)性騷擾案件都發(fā)生在日常生活場景中。除此之外,類似廟會(huì)等集會(huì)活動(dòng)也是性騷擾頻發(fā)的場景。《高邑縣志·風(fēng)俗篇》記載:“每逢廟會(huì),則聯(lián)袂接種而至者,男女雜沓,巷里為空。”湖南“共城小邑,馳情趕會(huì),肆志燒香,千百為群,如蜂如蟻”。衡州男女于佛誕日“攜巨燭往跪于壽佛前,名曰跪燭,男女雜處,老幼無倫。城中流氓見婦女稍美者,亦買燭以跪其旁,實(shí)為調(diào)戲,傷風(fēng)敗俗”。乾隆年間江南巡撫陳宏謀提倡婦德,在任期間禁止婦女參加廟會(huì)、春游等等活動(dòng),被當(dāng)時(shí)的江南士大夫批評妨礙小市民生計(jì)。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評論說,“治國之道,第一要?jiǎng)?wù)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游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嘩然,由是馳禁。”可見,清代官僚并非沒有采取手段強(qiáng)化性別隔離,只是最終政策以失敗告終。
當(dāng)社會(huì)層面無創(chuàng)造利于守貞的帶有性別隔離色彩的理想環(huán)境,國家又在制度上對貞潔進(jìn)行強(qiáng)有力的維護(hù)時(shí),婦女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她們必須守貞,另一方面她們難以在生活場景中完全屏蔽潛在的性騷擾。在這種環(huán)境下,為了能夠保住自己的名節(jié)、利用法律伸張正義,往往要支付無比慘重的代價(jià)。而當(dāng)代女性面臨的也是清代婦女處境的變體,不同的是當(dāng)代女性有了更多受教育機(jī)會(huì),思想覺悟更高,有能力爭取更多的話語權(quán),或許有機(jī)會(huì)改變自身處境,不讓羞忿自盡的悲劇重演。
 手機(jī)版|
手機(jī)版|

 二維碼|
二維碼|